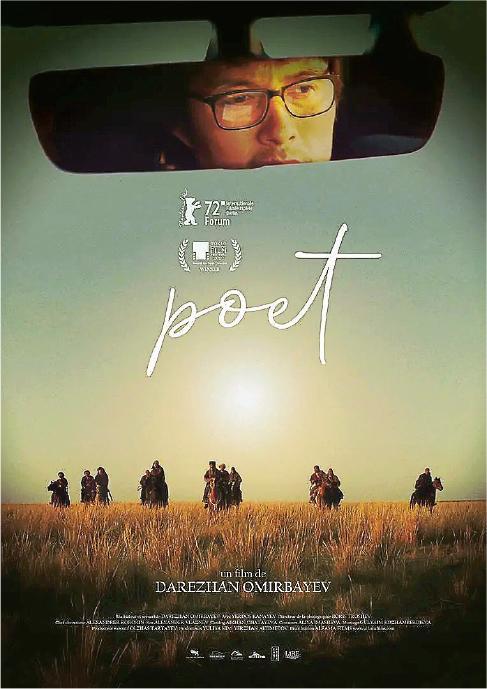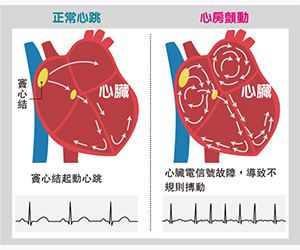【明報專訊】因為是報館小員工,所以亞洲電影大獎節目表上《古來詩人皆寂寞》(2021)開頭一句:「中年詩人迪達在小報社做文員」,對我來說有一種交換日常經驗的入場引力。但別的觀眾,又有什麼理由拋下簇簇星光的大製作,去看這齣攜着「冷門」兩字的哈薩克電影?放映前訪問導演奧米爾巴耶夫(Darezhan Omirbayev),他朝我點他的頭:「我當然可以拍攝音樂家、電影人或其他藝術行業,但當刻,文字承受最多的苦難。」一個異國窮困詩人在現世掙扎的故事,與你無關。然而,影像全世界下文字與語言的遺失,是你不讀詩不寫詩也掩不住的貼身危機。
年重複年地定居城市,常錯覺文化結晶自有永有:文學的書本、戲劇的舞台、建築的樓宇……那些東西,卻不根植地平線另一端的哈薩克。200多萬平方公里的亞歐大陸,大片平原湧向大片山嶺,那盤踞內陸國面積首位的龐然疆土,踏印着部落汗國的千年游牧;馬脊上,穿過風音,經嘴巴至耳朵一代一代流傳的,只有詩——「我們的音樂傳統很強,但其他方面的傳統很弱」,奧米爾巴耶夫解釋,「當整個民族不斷遷移,人們不會有機會去搭建或繪畫什麼」。
哈薩克語的電影原名「Akyn」翻譯過來大概是即興吟詩作歌的詩人,而在大部分游牧人口皆不能讀寫的歷史語境下,這詞彙具殊別的政治意味:為民族發聲,頌揚正義、揭穿邪惡,他們是人民意志的集體。理解到這一點的時候,也就明白電影為何以男主角一人分飾2020年的落泊詩人迪達及1846年被處死的詩人兼政治領袖烏捷米索夫(Makhambet Utemisov),詩在當代哈薩克陷落,不僅指向文學的衰微,更關乎一整個民族被趕下馬背、關進四面牆壁後的失語失根,那無法依黏歷史主體的深層斷裂。
科技侵蝕內心
如此災難,成因之一是西方馳驅而來的科技文明。劇中,迴旋於迪達如何在金錢至上的社會受挫、如何拒絕為工廠老闆作傳的主線之間,是大量電子熒幕的特寫鏡頭。「這些工具能給出一種當代的感覺,看看四周,到處都是熒光幕——」坐在酒店房間,奧米爾巴耶夫的視線由掛牆的電視機,轉一圈至掌內的手提電話,「作為無法迴避的生活一部分,它們應該被如實呈現於電影裏」,「其次,它們打開了另一重視覺和符號層面的維度」。那維度,嵌於1991年脫離蘇俄獨立、因豐富石油資源而致富的哈薩克共和國,直指物質發達後如河水一樣流過人們眼球的雜亂資訊。
想起劇內,迪達女兒寧願塞起耳朵玩電子遊戲也不願與祖母共處,老人家沒事做,只能盯着電視機不停轉換頻台。在我看來,奧米爾巴耶夫不是強求人們回去日夜念詩的草原歲月,他批判的,只是人們被過量資訊掏空,內心變得虛空、麻木、冷漠,遺缺一種關注外界以至自我真實的「詩意」。如同臨近結尾一幕,迪達看着勞工爭取權益的電視新聞,先關掉機器,然後走到窗邊俯視街頭掠過的一場毆鬥,最後凝進鏡子半身的倒影。即使沒有畫外音,觀眾也彷彿聽到那內盪的吶喊:什麼是詩?為什麼要寫詩?問題的答案,靜靜反照於烏捷米索夫的詩人生命,死前,畫面響起他的吟誦:
O lapwing bird in the sky,
You have also lost your lake
A falcon took it from you
I was robbed of my country
All because of Zhangir Khan
Should I speak or not
The grieve will never end
For the rest of my days
(節錄自《古來詩人皆寂寞》英譯字幕)
革命失敗。同伴離世。烏捷米索夫悲慟而輕柔地與鳥傾談,彷彿要把靈魂附於那些自由飛翔的物種上。詩是意志。是尊嚴。是被鷹奪去湖的田鳧鳥。不受名利誘惑,不為政權效力,他最終被蘇丹派來的殺手斬首。鏡頭緩緩搖動:沾在匕首上的血迹被草草冲洗,妻子埋在黑裏嚎哭。電影來到結局,迪達有所覺悟似地打電話給那個只懂錢的朋友,說,他不要豐厚酬金,他不會為資本家寫片言隻字。
語言之間的張力
佇立在詩的母題上,電影不留力地直抒英語全球化下的憂慮。一開始,奧米爾巴耶夫便客串報社員工,嘆道:「現今即使在法國,也有一半科學論文是英語。這意味着即使是主流的、強大的國家,它們擁有偉大的語言和文學,也正面臨衰敗。哈薩克語又會怎樣呢?」依沿前蘇聯國家的影子,哈薩克現時並行俄語和哈薩克語。俄語在國際較通用,但奧米爾巴耶夫認為,少數的哈薩克語也十分重要,「如果哈薩克是一棵樹,它要成長且結出果子,就需強壯的文化根部,比如語言」。
話雖如此,執導前打滾於學術界和評論界,奧米爾巴耶夫深深明白,實際情况不容許哈薩克人多用母語。「全人類愈來愈一體化,就如歐盟,或其他大大小小的國家彼此連結。因此,人人都要說多一種語言。試問,數學或物理學者想向國際發表研究成果,為何用哈薩克語而不用英語?我兒子在IT行業工作,他說幾乎所有國籍的人都用英語溝通。」他有點自嘲地笑:「我不是一個好例子,我不會說英語。」我們相視微笑。當刻的對話全由監製在旁即時俄譯英。
外地與本地交界的文化張力,默默透滲在電影內。一方面,全劇努力鈎沉哈薩克傳統的詩性質感,另一方面,又積極地從別國資源汲取文學養分。譬如,劇內結巴女生站在空無一人的演講廳,為迪達讀詩的關鍵一幕,便是發想自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Hesse)的短篇小說〈作家之夜〉(The Author's Evening),奧米爾巴耶夫改編了作家被觀眾輕視、嘲弄的主情節,揑塑成影像的情感骨幹。又如,他本人十分鍾愛日本的三句短詩俳句(haiku),閒時會動筆寫,甚至覺得所有導演都應從中感悟鏡頭美學。江戶時代的「俳聖」松尾芭蕉便是他隨手拈來的例子,「他有首著名的俳句『秋天來到/訪你的睡耳/枕之風』。它早自成一個場面,像一部小電影—— 一個人睡在枕頭上,被風晃醒,然後鏡頭搖上去,是一棵秋天在掉葉的樹」。
說到底,語言一體化是無可抗拒的世界趨勢。眺向國際,不忘本土,如何巧妙且平衡地張弛兩者,考驗的是創作者的眼界和適應力。「說不定百多年以後,在兩大強國之間,我們都只會說中文或英文呢。」奧米爾巴耶夫半玩笑半認真地說。
鏡頭下的詩學電影
電影既然對焦詩人,那麼,無法迴避的頭痛問題就是:文字與影像,兩套性質截然不同的符號系統,該怎樣互換?文學「詩意」與電影「詩意」各自對應怎樣的語言?奧米爾巴耶夫往昔求學,曾以意大利導演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65年提出的理論〈詩學電影〉(The Cinema of Poetry)為研究題目。柏索里尼指,由於電影沒有方言、句法、語彙等文學區別,故其詩意來源,只可透過介於客觀被攝物和主觀攝錄者之間的影徵(image-signs)來提煉。簡單來說,就是奧米爾巴耶夫直接向我拋出的英文詞彙:「style(風格)!」
「很多電影不直接引用文學的詩,但它們的拍攝充滿詩,非常有詩意。」鏡頭、光線、音樂、剪接、場面調度、演技等等,皆形成風格差異的影徵。而《古來詩人皆寂寞》最耐人尋味的迹印之一,恰是各種蒙太奇剪接下,曖味織合的夢境與現實。例如,迪達和同事們從門縫窺看桌上全裸的性感女秘書、迪達把大賣場所有電視畫面換上自己的詩集訪問……在戲院看第二次才驚覺是一場夢。這些片段,與電影呈現的現實幾近無異,只有大塊大塊的藍光,或偶爾不合理的聲音串連,或迪達睡醒的惺忪的臉,方使觀眾提心懷疑那條表意識與潛意識的界線。種種影徵穿在一起,凝定難以言述的無形詩感。記得映後工作坊,有觀眾提問某一幕漠上爬過的烏龜是什麼意思,奧米爾巴耶夫這樣回答:「我也解釋不到,只是覺得那一刻需要這個畫面。」
異於他眾的風格,也充分反映在奧米爾巴耶夫擇人的方法。他作品的主角從不是專業演員,專業演員往往是輔助的配角,「當然,用非專業演員是很危險的事,比如他們不小心就會直望鏡頭。但我選擇某一演員,是因為他們的真實性情適合角色,而非他們演技過人」。詩意埋在表象以外。恰如影評多指電影缺乏細膩的臉部表情,但我的觀影經驗,確切感受到人物自內部渾散的一種情緒,濃稠的,苦澀的,鬱愁的。比如飾迪達的演員是哈薩克歌手,或因這緣故,他舌腔吐出的詩行奏律特別動聽,而他也許更明白母地的語言失落意味着什麼;又如結巴女生是現實中奧米爾巴耶夫的學生,那皺成一團的緊張神態與話語間的真摯,異常觸動。
亞洲電影大獎的獎項名單,沒有長長的哈薩克名字。僅只一場的放映,席位填着觀眾,但坐不滿,瞥到些零零落落的椅子。我想,奧米爾巴耶夫不會太介懷,因為有些應被珍視的價值不能以大眾或小眾來劃分。戲裏,無人出席的讀詩會上,結巴女生如此勉勵迪達:「你的詩句……在我生命最艱難的時刻……賦予了我無比力量。這晚,只有很少人來到,不要難受……謝謝你,這天來到這座城市……並在如此艱難的時代,選擇成為一位詩人。」
info:奧米爾巴耶夫
1958年出生於哈薩克江布爾區。畢業於哈薩克國立大學應用數學系,曾在塔拉兹和卡拉套城鎮任職程式員和數學老師,兩年後因興趣使然,轉而投身電影行業,在1980年代相繼進修導演和評論相關課程,並編導作品如Killer(1998)、About Love(2006)、Student(2012)、Last Session(2022)等等。其藝術成就備受國際影壇肯定,如長片《古來詩人皆寂寞》(2021)獲第34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大獎、第16屆里斯本和辛特拉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