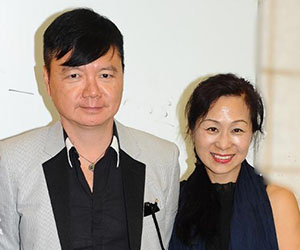【明報專訊】在法國的建制體系中,存在着一個具有超然地位的機關,它的名字叫憲法委員會(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法國第五共和於1958年成立時,憲法委員會隨之誕生,以維護共和憲法為目標;委員會由9位資深法學家組成,經總統和上下議院委任,地位上凌駕所有政府和立法機關,監察政府運作會否破壞共和民主及三權分立。委員會最初較為象徵式地存在,至1970年代起,它的監察愈趨實權化,經常在立法過程的最後關頭把關,否決了不少違反憲法、損害公民社會或侵害人權的法案。對媒體而言,委員會猶如法案審議的終極法庭,所以委員會又被稱「憲法庭」,而與會的9人常被稱作「九大智者」(Les Sages),縱使不時遇到總統出言威嚇,他們亦會無動於中;因此,每當社會陷入巨大政治危機,人們焦點便會放在這9位智者身上,希望他們能在最後關頭扳倒具爭議性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