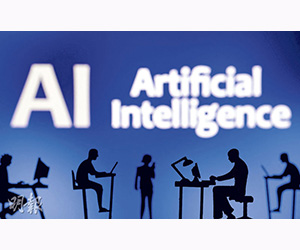【明報專訊】那天忽晴忽雨,用黃燦然的說法,應該是傲慢的詩神也在旁聽,怕他和許鞍華詆譭自己。紀錄片《詩》早前於電影節首次公映,廣邀本地詩人與文學界數代師生出席,但主角並不是導演許鞍華。她笑瞇瞇問道:「你最想問為什麼選他和廖偉棠吧?」黃燦然聞言大笑:「如果要論資排輩,看誰得過多少獎,地位又是怎樣,這樣的電影最多就是拍給詩人自己看,外面沒有人會理你。」剛從深圳回港的他,點起那天第一根煙。
儘管是一部關於香港詩人的紀錄片,但不想只傳頌於詩人圈子裏。詩人只是眾多觀眾之一,電影本身有它的敘事方法。疫情期間,許鞍華坦言停下來重新思考,如何好好拍電影,《詩》用意很明確:香港的故事,從詩出發,落在兩個不再在香港生活的詩人身上。
紀錄片以詩人黃燦然和廖偉棠的訪談為主軸,他們一個出塵隱居,一個積極入世,體現了當代詩人的兩種生活形態,但有一共通點,黃燦然早已「經濟流亡」回深圳生活,廖偉棠則幾年前與家人移居台灣。許鞍華承認有被質疑:「很多人問我,甚至說很奇怪,他們又不在香港,又不是香港人。但我說很多香港人都不在香港出生,我也不是呀。而且,現在這個世界還需要你在那裏才寫到那裏的東西嗎?我覺得已沒有地域的界限,將心靈的界限劃在哪裏,才是最重要的。」
黃燦然、廖偉棠雖是中年詩人,對她來說卻是下一代的「新」詩人。「因為我是被《中國學生周報》湊大的,陸離、小思、西西、戴天、崑南,跟我同代的作家,我基本上都認識。」但接觸到黃燦然這些「新人」,令許鞍華大感興趣。「他們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不像我們那一代,譬如經常說要喝酒,哈哈哈。古龍就經常喝酒了。但他們不是,不會非要活得像《人間失格》那樣才覺得自己是詩人。」笑罷,她認真解釋起來:「他們知道自己是詩人,但他們很實際,不會說要放棄了生活,然後才去寫詩。雖然他自己有講到明,寫詩是不求結果,但是都要生活,他們自己有一套,有些做,有些不做,不會全部都不做,令到他自己很潦倒。你要做一些很idealistic的事,就同時要保持自己的狀况。我覺得這種看待生活的平衡態度是很值得學習。」
許鞍華形容,黃燦然的詩貴乎一種很難得的平衡:「詩是主觀的,詩人會把詩人這個位置看得很重。但他的詩,雖然全是他的觀點,表達的東西很主觀,給你的感覺卻是客觀,對一些現象的剖切很理性,同時它又很感人。不覺得他很自大,因為我是黃燦然,所以我會看到這些東西。」
「別人說我的詩,我就唔好意思了。」黃燦然笑着撚一撚手上的煙。許鞍華轉過話題:「但另外有些人會不明白,甚至我們的investor都問,為何不用廣東話讀他們的詩?黃燦然自己一讀,就讀了普通話。反而廖偉棠自己一讀,就讀了廣東話。其實我不覺得有問題。」
「說到讀詩,就有點意思了。」黃燦然徐徐答道:「有些大陸人以為我是香港人、廣東人,我的母語是廣東話。其實不是,我的母語是閩南話,但閩南話本身方言的成分太大,讀出來都要經過一輪翻譯,那就不自然了。廣東話讀詩是特別好聽,但對我來說也是絕對不自然。因為我廣東話不準,我是十幾歲才來(香港),廣東話主要是以前在工廠學的,只剛剛夠應付。用廣東話讀詩,我就會緊張,每一次朗誦之前都要重新再去做一次練習,對我來說是完全不自然的。普通話不是我的母語,卻是各種不自然之中,可以最自然朗誦的選擇。」
新詩與舊褲子
黃燦然接着又說:「自然和不自然之間,還有一個很微妙的東西。之前我跟人說,我穿的這些舊褲子,是我媽咪、我妹妹幫我補,後來我搬去深圳之後,就去鎮上找裁縫補,我穿這些,說新潮又好,老套又好,對我來說很自然。但如果我去買一件穿窿的褲,回來再補,你在街上看到我,表面上差不多,實際上差別很大,我自己會表露出一些自己知道,人家都可能覺得不妥、不自然的感覺。」
事實上,許鞍華也在紀錄片裏跟着黃燦然去縫補舊褲子。訪問這天,他同樣是穿著這條早已縫補多遍的舊褲子。只是有點不明白他為何對舊褲子如此執著,直到他這樣說:「任何場合,連我去電影節都是穿這些,我不會不自然。我穿這些,是我媽咪替我補的,我就會很自然。包括寫一首詩的自然和不自然,都跟這些有關。只要你寫的東西很誠實,你就會好像這條褲。但表面上有些詩寫得很好、很深,其實有些東西是真的不自然,未必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但大家可以聞得到。」
黃燦然對詩人身分看得極重,言談間甚至有一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詩人高的孤傲。譬如說,他就很介意別人嫌詩人頭銜太虛無縹緲,改為形容他是翻譯家。黃燦然翻譯詩作甚多,包括《詩》裏描述廖偉棠在台灣大學教詩,引用布萊希特和策蘭的詩句,皆出自其手。然而,煙不離手的黃燦然,心之所往是窮一生做詩人。但詩人是否非窮一生不可呢?
他們都說,現實就是想不窮都難。「在外國你也找不到,除非有副業,或者得獎,可以賺多少少錢。」許鞍華說。
詩神是很妒忌的
「就看你願不願意付出代價,其實都可以去大學做教授,尤其是外國,然後繼續寫詩。但是,我始終覺得,詩人是……」黃燦然突然打住,思索了一下,續道:「他本身精神很高,但他的身體是很世俗。我曾經在寫波特萊爾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詩人可能是半神,即是說,他會高出世俗,但不是說他的身分高一點,而是他能夠俯視人間。詩人始終都是一個肉體和世俗的人,詩一定和這個世界緊緊相連。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就不是詩了。但相反,如果你沒那些精神性更高的東西,你就不要寫詩了,你去寫專欄、寫散文。」
許鞍華大笑:「我幾想challenge你講這件事,不過想不到原因。」
「因為我真的有十幾廿年都在報館裏做這些。如果你為了供樓買車,你搏命寫,寫很流行的書,不是說實際消耗了多少時間,而是你寫詩方面的能量會慢慢降低,最後可能不見了,再沒有辦法得到。」黃燦然早年於報刊國際版做翻譯,常感抑鬱,認為被文字工作反噬,磨蝕了心志,「我寫過很多詩,尤其在90年代,經常控訴世界對我有很多精神上的剝削,它奪走了我的時間精力。因為那時候,我老婆、女兒都來了,我又要租屋,要生活,終日經常都想着錢,是真的很辛苦,撕裂得很厲害」。
「我始終覺得,即使是暫時的,都不要暫時太久。久了就變成永久。但我要還錢給人,當然要搏命寫。那時候有些親戚朋友信任我,願意借錢給我,縱容我去買樓,我買了樓,第一時間是想快點還錢給他們,一還完這些錢,即時不想再賺一分錢。」與其說淡泊名利,黃燦然是心裏害怕為名利而寫,最終寫斷了自己詩。
「在89到90年,這兩年時間,我在工廠上班,每一天早上10點做到晚上10點,我一天唯一可以讀英文的時間,就是中午那一個小時。我半個小時吃飯,15分鐘睡一睡,還有15分鐘,就用來讀英文社論,是為了保持我的英文。這個很重要,如果中斷了一天,我可能中斷兩年。中斷兩年,可能從此就不會繼續讀英文。」說罷,他兜了個圈才言歸正傳:「我覺得寫詩也是這樣,可能95%的時間和精力是用來應付生活,但我始終有5%不會變。而且我覺得這95%付出去,只是為了去換5%回來。我是這樣想。」
黃燦然笑言,後來離開報館,搬回深圳「經濟流亡」過活,情况剛好相反。「我可以有95%都用來做詩有關係的事情。如果當初連那5%都沒有,以後就再沒這個機會。因為詩,是有詩神的存在。詩神是很妒忌的,如果你背叛了他,到你想回來,他不會給你回來。你不要背叛他,你不要覺得等我搞好了生活,等我有錢有屋有車,然後我再回來寫詩,沒有了,到那時就什麼都沒有了,絕對不會。我很早就認知到這件事。如果我要改善生活,我是一定要一邊寫詩一邊改善,不可以說改善了之後,再回來寫詩,你沒這樣的機會。」
說着,黃燦然不無感慨,尤其在中國大陸,這種情况見得太多,他說:「很多詩人都是這樣,早在90年代就所謂『下海』,然後賺了很多錢。有錢了,後來甚至會支持一些詩刊,幫人出詩集,想着自己又可以這樣繼續混入來,不可以了。沒機會了,有很多錢都沒用,你可以幫很多人出詩集,辦很多詩歌活動,但是你沒有就是沒有。你再寫,都沒有用的了。精神沒有了,就玩完了,你寫的就只是文字,不是詩。詩神總是『精』過你的,你以為你『精』得過他?沒有的。寫詩沒辦法這樣計算的。」
黃燦然眼中,詩人抬頭有詩神,許鞍華頭上則可能有電影之神,《詩》這部紀錄片是她執導生涯一次為時未晚的轉捩點。「其實我們也常說,若純粹去拍商業片,你就回不了頭。以前拍戲,nothing to be ashamed是很多時要賺錢的,但《詩》不需要很計算怎樣回本,給我自己的感覺,跟以前是兩個階段。這部戲,我現在是為了想拍而拍,不是為了搵食。」
許鞍華欣賞黃燦然的詩作,說到底亦有幾分羨慕他作為詩人而不被動搖的信心。「他很清楚自己的追求,以及他要做到這件事所要作出的妥協和平衡。至於我呢,就一直煠吓煠吓囉,總是拍一部找一部。然後下一部沒了、衰了,又再找下一部。我不是很知道何時是做藝術,何時是商業。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我沒有好好地退後一步去想,見一步行一步,載浮載沉,我太忙,心太亂,但不可以這樣原諒自己,再忙你也要搞清楚其實最想做的是什麼,你可以做到什麼。」
不過,這幾年疫情令一切停擺,卻讓許鞍華深感不爭氣:「由拍《瘋劫》開始,到現在40多年,原來我拍feature film是沒有什麼長進的。對於怎樣去看一件事,拍一部戲,我都是用回以前那一套,所以這幾年覺得很悶了,都不想拍。所以,要不就不再拍戲,要不就好好地重新想過,到底想怎樣拍,想表達什麼。可能我已經沒什麼時間了,但事實就是這樣。」
從影40多年來營營役役的許鞍華,就以另一種形式換回那最重要的5%。從小到大都不敢表露自己喜歡看詩的人,結果就拍了一部以詩為名的紀錄片。「我是想推廣這個戲,通過它讓大家對香港文化,尤其是詩,有所認識,也認識到詩人其實是怎樣生活。可能再不是為了我自己,我沒有以前那麼緊張和自我中心,不知道是否叫做進步了。」
好詩無定義,壞詩有
許鞍華與黃燦然因詩與電影而結識,黃燦然形容是一見如故,但對於自己的創作,他們畢竟年紀有別,處於人生兩個階段,心態上端見一些細微的不同。譬如說,許鞍華偶然掛在嘴邊,怕自己不夠時間完成想做的事,但黃燦然不介意用所有時間去等,等自己老去。
「自從我拍了《詩》之後,其實有幾個問題我很想再研究,但就不知道還有沒有精力。比如說詩的翻譯,詩的語言、韻律,現在寫詩的趨勢。我看詩很多時候是憑感覺的,但不是說我喜歡就行,其實是要有人去表達,要講理性。」許鞍華說。
「但其實詩本身就應該是這樣嘛。」黃燦然答道:「寫詩是沒有辦法計算和量化的,但詩要來的時候,你不知道它何時來,只能夠,好像我這樣守着守着,有一天它真的來了,是有些運氣,哈哈哈。」他坦言,搬到深圳洞背村後寫了兩本詩集,但過去兩年確實少寫,而且好幾本詩集都(礙於出版審查)未有機會出版。「但我現在又不急。想到二三十歲的時候,最怕就是自己寫不過四五十歲,因為你看整個中國的新文學史,詩人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就只是一種青春期的詩,或者很青年的詩,沒有進入過中年、老年,那種成熟思考的詩。」
「但你要至少要活到四十歲之後還在寫詩,過了五十歲你還寫詩,過了六十歲你還寫詩。我們寫詩的時候沒這些先例,你說大陸有政治鬥爭,但台灣沒有,即使是台灣那種環境,像瘂弦、鄭愁予,很多人後來都再沒有寫詩。我最怕的就是這樣。我想整代人都有這樣的焦慮,可不可以寫到四五十歲呢?起碼過了五十歲,如果寫到六十歲,就不用那麼擔心,因為都寫了二三十年,中年、老年你都有經歷了,你的詩就很成熟了。」
所謂的老去,最終可能只是為了等某些事情遠去,有足夠的距離,回頭撿拾年輕時寫的「壞詩」。「無論是什麼事情,包括詩,都會形成建制,固化你的觀念。」他忽然想起一首舊作:「我在1986年寫過一首詩,叫〈泉州〉,就是我的故鄉。那時我女朋友住在那裏,這首詩十幾廿行,很短,幾乎就是寫一個地址,是我女朋友的家,就是這樣。那時泉州是個小城市,誰知道,我那時寫詩,也是沒有人知道的。但幾十年後,我發現它有一個很獨特的平靜語調,我永遠都再得不到這個語調。很有趣,我對它印象很深,但我一直沒拿過出來。」
稍頓,黃燦然試着解釋:「因為有時代的審美潮流,你知道當時沒人像你這樣寫,所以你會覺得心虛。你把詩寫出來,但你不是用自己的觀點去看詩,你會用當時一些詩的標準來判斷,包括文學獎,或者現在最流行哪幾個詩人,你像誰,你的詩用到什麼意象,你以為詩人很獨立?其實不是,他們很小圈子。」
「一個詩人可以模仿很多人的技巧,不斷練習,但有一些時刻,你突然寫出你自己無法控制的詩,那可能就是對你最重要的時刻,但你寫出來的時候,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如果過了幾十年之後你再重新看,那種獨特就是因為我很誠實,甚至寫出那時候自己都看不起的詩。寫詩要忠實到什麼程度?就是忠實到你自己都覺得寫得不好。」
「真正的好詩是無法定義的,但首先你不要寫壞詩。相對來說,壞詩比較容易看得出,有些是技術不行,或者寫陳辭濫調,或者用政治那些來支撐自己,或者用社會的角度支撐自己,這些都可以被看出。」黃燦然接着說:「但是,我想就是誠實,誠實是最重要。在所有藝術創作裏都一樣,就像我剛才說的補褲子這個例子,因為你是誠實的,你有自信,它有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你寫出來,人家一看,起碼會說是不錯的詩,它好到什麼程度,這會隨時間而變,之後會有什麼潮流,想來也沒意義。但你寫出來,它不會差。」
不想被看見的詩人
作為紀錄片的開場白,其實還訪問了飲江、淮遠、鄧阿藍等詩人,不過篇幅只有十數分鐘。黃燦然點起下一根煙,「講真都想看多一些,但我知道這關乎電影的結構,要見好就收,才會看得那麼過癮。可能多幾個鏡頭,你又覺得沒那麼好玩。你不覺得開頭十分鐘很矜貴嗎?」
「是矜貴呀,現在再約他們都不肯出來,哈哈哈哈。」許鞍華承認,不是所有詩人都像黃燦然,有些是很抗拒公開訪問。「他們很客氣,但問題是絕對不妥協,哈哈,不見你就是不見你。得閒可以跟你去行山,但就是不做你訪問。」
黃燦然忽道:「但我是絕對理解老一輩詩人的固執。很簡單,因為詩人見到自己的影像,就覺得自己是幾咁面目可憎。詩人不是給人看面容的。鍾意看到自己的那些人,是藝人、演員。」他接着又說:「詩人是用文字,如果用影像,那根本就不是他們。我經常說,我最不喜歡人家直播或者拍視頻,我不喜歡。你影像做得再好、再專業,但詩人就是不想被人看到,詩人是看書。」
許鞍華不禁反駁:「我覺得你這想法過時了,而且你講嘢那麼好,不說浪費了你。」
黃燦然隨即搖頭耍手:「我最怕做活動那種事。」
「但如果你是不介意給人看,可以豁達到被人看見,你也可以表達真正的自己,你就真係掂。這個時代你無可能不被人看到的。」許鞍華說。
所以,黃燦然還是答應了許鞍華,拍《詩》。隱居深圳之後,黃燦然婉拒了絕大部分的採訪及拍攝邀請,或者拍了自己都不想看。《詩》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而且黃燦然與廖偉棠都雙雙出席了首映活動。「我都怕他們不來。如果來了就表示他們接受這件事。因為他們多數不容易露面,很高傲的。」許鞍華笑着望向黃燦然。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最重要並非它得不得到香港詩人認同,最重要是,它會衝出文學圈子。」黃燦然如是說。「就像我最近研究的卡瓦菲斯,他第一步,就是詩,只影響詩人,到再版的時候,相隔差不多10年。它已經入到文學,即是比較大的文學範圍,到第三次,就是最近兩年,它已經入到文化界。從詩到文學再到文化,接觸的那個層面已相差了很多。甚至我一個朋友去大理,他看到好幾間酒吧,都有擺放卡瓦菲斯的詩集。一個外國詩人的詩集,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產生影響。我也希望,這部電影能夠不只對詩人,可以跟文化界有一點點連結。平時喜歡看電影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注意香港詩,他們都能夠來看,這樣就最好了。」
「都未知得唔得呀,那晚首映其實全部都是『自己友』,可能只是我們想得太美好。」許鞍華不忘潑冷水。
說完沒多久,那天午後忽又倒了場暴雨,落湯雞似的詩意。詩神喜怒難捉摸。
■答:許鞍華
電影導演、監製、編劇,曾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紀錄片《詩》為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
■答:黃燦然
詩人、翻譯家。曾任報刊國際版翻譯。著有詩作《發現集》、《奇蹟集》及翻譯作《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致後代:布萊希特詩選》等
■問:紅眼
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著有小說集《壞掉的愛情》、《伽藍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