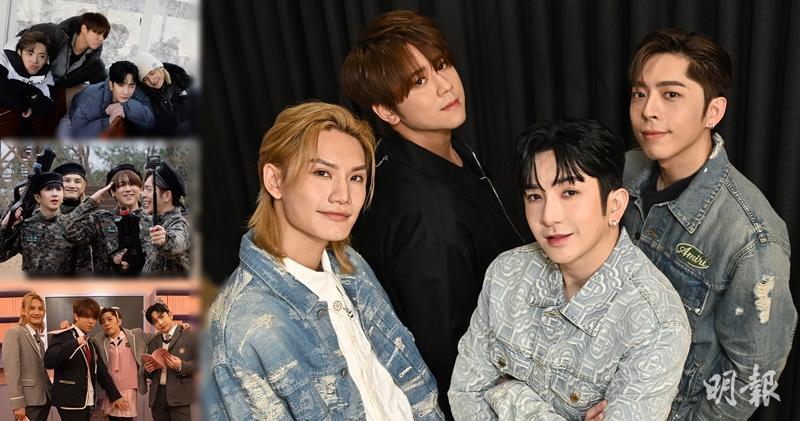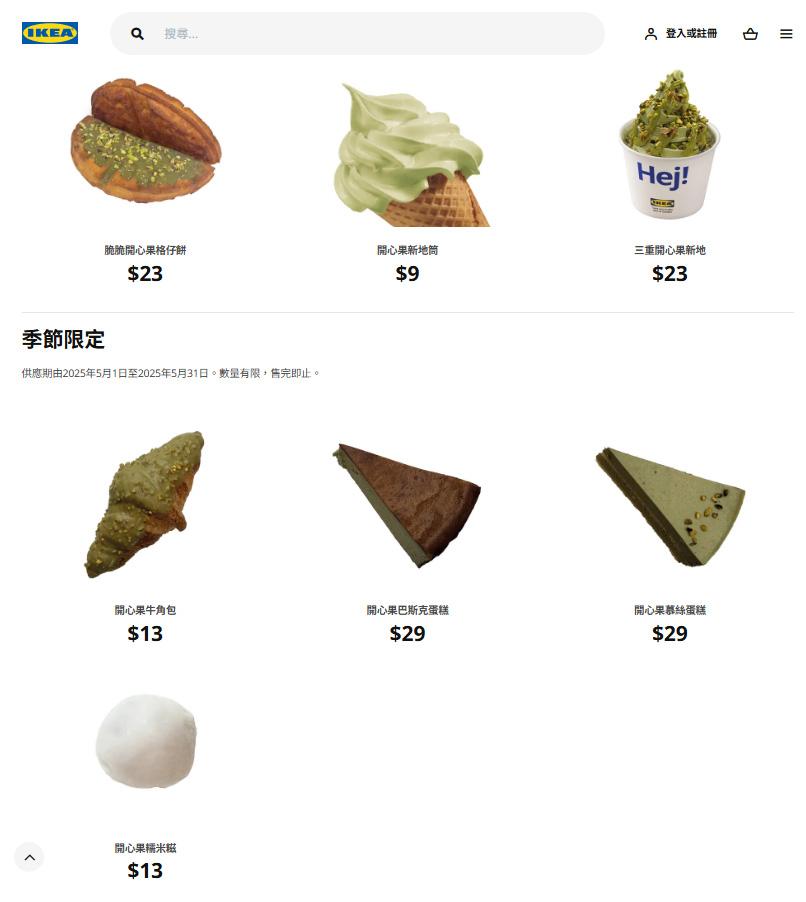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M+上月開幕的展覽「宇宙最強之懸浮者──Lauren O」榫接去年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繼續從虛構中滋出那名為「Lauren O」的1960年代美國社運分子兼懸浮異能者。這樣的偽紀錄片或偽檔案展並不是說分辨真假不重要,相反,正因為兩者疊合過於巧妙而使人深深迷惑,不得不召喚起清醒的反思:真實是什麼?歷史是極多層敘述的矛盾體?就如藝術家徐世琪指向的「懸浮」不是什麼科學現象,那介乎於升降之間的不可思議姿態,是一種人類本源的不甘心——「不甘心受地心吸力限制,與生俱來的一些反抗」,反抗再反抗,不要甘於經驗世界壓向你的所謂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