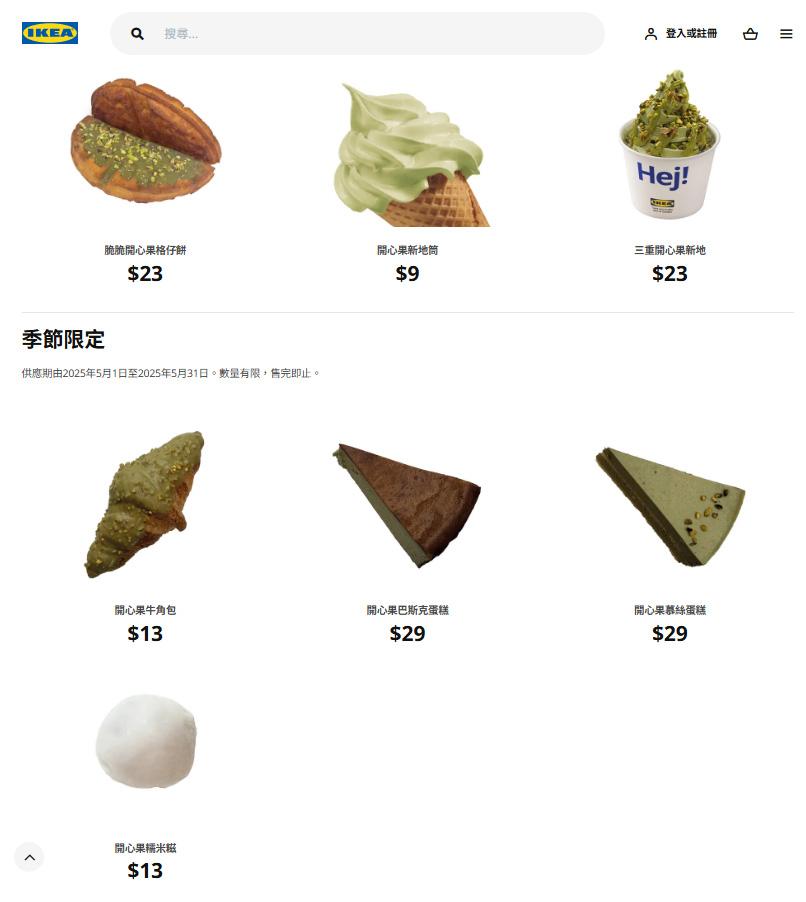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剛逝世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雖然享譽國際,但在故國捷克一向不受歡迎。據說,捷克老一輩人有個笑話:「哈維爾坐監,然後當了總統;昆德拉去了法國,然後當了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舉世知名的異見領袖,又是出色劇作家,由異見人士蛻變成總統的故事幾近童話般完美;1975年流亡法國的昆德拉則力拒「異見人士」的標籤,強調自己是小說家,甚至用法語寫作,跟捷克的距離愈來愈遠。一個留下抗爭,一個離開寫作,兩人都只是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路而已。
昆德拉曾強調不喜歡把自己的一生說得像通俗劇(melodrama)般,那麼要說他的故事,自然得由其小說入手。
昆德拉曾經說,小說就是作者透過不同的「實驗性自我」——即角色,去探問關於存在的各種大課題。其最著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也如是。跟昆德拉本人一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男主角Tomas不容於政權,但跟昆德拉不一樣,Tomas選擇留在捷克。蘇聯1968年8月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所開啟的自由風氣告終,大批知識分子移民,Tomas跟妻子Tereza也到了瑞士,本來是一片新天地,但Tereza一天不辭而別重返捷克,Tomas為了她毅然放棄瑞士的工作回到捷克。Tomas的情婦Sabina則遠走他方,跟其他流亡者保持距離,甚至隱瞞捷克人身分,因為她很怕外國人先入為主,把她當成受逼害的藝術家,將她一直逃避的kitsch(惡俗)加諸她身上,這正是昆德拉流亡後的寫照。
留下來的Tomas面對不少掙扎。先有秘密警察拿他的舊文章威脅,要他發聲明指證編輯,Tomas拒絕,寧願不做醫生,因為強權只有興趣壓迫知名人士,如果他只是個普通人便不會有人理會他了,於是Tomas當了抹窗工人。但盯上他的不只是共產黨,還有異見者。一天,Tomas跟前妻所生的兒子連同前編輯來找Tomas聯署促政府釋放政治犯,Tomas拒絕簽署,認為簽名根本無用,而兒子逼他簽名的咄咄逼人態度也跟共產黨政權無異。更重要的是,他所有決定只建基於一個條件,就是不傷害Tereza。他救不了政治犯,但可以讓Tereza快樂。
這兩個段落很難不令人想起昆德拉自己。昆德拉曾是熱心的共產黨員,1968年短暫的布拉格之春他跟其他知識分子熱心論政。惟蘇聯入侵後,捷克撥亂反正,他失去教席,書籍從圖書館消失,遑論發表文章,連音樂家父親及於電視台工作的妻子都受牽連。他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監視,跟妻子聊天也要離開寓所避開監聽。據《世界報》4年前一篇關於昆德拉的長篇報道,捷克秘密警察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關於昆德拉的監視檔案有整整2374頁之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Tomas由醫生變成洗窗工人,昆德拉則嘗試當的士司機但不成功,最後用假名在青少年雜誌寫星座運程,也寫了一部劇作。在這段期間,昆德拉曾拒絕簽署一份釋放政治犯的聯署,該聯署發起人正是哈維爾。
哈維爾跟昆德拉命運的交集始於1950年代。富家子弟哈維爾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背景,屢考不入大學,唯有投考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的電影學院,當時昆德拉在該校任教,並指導哈維爾應付入學試,但哈維爾還是考不上,1957至1959服兵役。60年代,哈維爾開始以荒謬劇建立名聲,跟昆德拉都在文壇享負盛名。
筆戰
布拉格之春以蘇聯入侵告終,不過政權初時還讓捷克人享有公民自由一段日子。1968年12月,昆德拉及哈維爾展開一場筆戰,涉及兩人對捷克未來及反抗的迥異立場。昆德拉發表了一篇名為《捷克的命運》的文章,認為捷克作為一個小國,歷史上面對不可逃避的限制,但不代表沒有希望。他認為,蘇聯入侵後捷克並沒有失去一切,甚至還有希望,呼籲繼續團結一致捍衛布拉格之春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哈維爾一個月後發文反駁,文章題目用上昆德拉的原題但打了個問號,質疑所謂「愛國者」無法面對現實時便用過去來逃避。他稱,「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團結是虛幻的,布拉格之春的新風氣並沒有什麼特別,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其他文明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同意小國的命運,指捷克的命運是掌握在捷克人手中,又稱要以某些具體及危險的行動表達立場。
昆德拉1969年3月寫了一篇名題為《激進主義及表演狂》的文章還擊,可以說是對哈維爾的人身攻擊,聲言哈維爾的抗爭只是表演狂,純粹站在道德高地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篇文章也是昆德拉離開捷克前最後能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捷克隨後的發展證明昆德拉的評估是錯的,昆德拉和哈維爾都被政權從文壇趕絕。昆德拉流亡法國,政權求之不得;政權當時還給哈維爾發護照,希望他也離開,但哈維爾拒絕,繼續積極政治參與及領導抗爭,發起「七七憲章」運動,不時遭問話和入獄。歷史的發展最終出乎哈維爾及昆德拉的預期。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捷克學生示威招來鎮壓,激發更大規模示威,捷共見大勢已去,跟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會談,哈維爾12月當上總統。
不少評論說,昆德拉後期遠離政治,更極力否認自己的著作有政治意味,跟該次跟哈維爾的筆戰不無關係。哈維爾不滿昆德拉對反抗的犬儒態度,在1986年在Disturbing the Peace中,他提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omas拒絕簽請願書的段落,強調示威是有好處的,讓政治犯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並沒有被忘記;抗議也是公民社會重新挺直腰骨的開始,但哈維爾仍強調,自己很欣賞昆德拉的小說。1992年,哈維爾赴巴黎跟昆德拉敘舊;2008年,捷克有傳媒指控昆德拉50年代曾是告密者,哈維爾立即為昆德拉維護。雖然意見不同,但哈維爾到底沒有離棄老朋友。
勇氣
對照昆德拉與哈維爾,昆德拉的故事沒有哈維爾般精彩,昆德拉的政治判斷也惹人疑問。哈維爾的道德勇氣贏盡世人崇敬,語言擲地有聲,成為不少異見人士的慰藉;反之,昆德拉的語言卻滿是悲觀及嘲諷。昆德拉一直強調自己是小說家,自言小說便是不斷提出問題。提問不僅令極權不安,甚至連反極權者都會不安,正如關於Kitsch的批評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抗爭者、西方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Sabina,既受不了共產黨千篇一律的遊行,也受不了巴黎聲援遭蘇聯入侵的捷克的遊行。昆德拉的小說從沒有給答案,更沒有紮實的金句。就算那句在《笑忘書》中不斷被傳誦的金句:「人與權力的對抗,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也只是美麗的誤會。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談到這金句,稱讀者往往首先在小說中找到已知的東西,以為《笑忘書》的主題便是奧威爾關於極權政權加諸於世人的遺忘。當然,這是《笑忘書》所觸及的,但昆德拉更想探索的不止是政治的記憶與遺忘,而是人類的遺忘現象。
當然,這些抽象思考有沒有意義可能因人而異。不喜歡昆德拉的理由更多是抱怨他沒有勇氣留在故國抗爭,還要質疑抗爭的價值。不過,昆德拉選擇流亡是懦弱嗎?昆德拉到法國時已是46歲,由一個小國遷移到一個文化大國,還要用法語寫作,這其實需要很大勇氣。
哈維爾留在捷克毫無疑問是勇氣的表現。異見人士之路從來艱難,堅持是否一定會有完美結局,只要看看各地的異見人士的命運便知道答案。昆德拉對抗爭的疑問也不是全沒理由,他始終相信,文學對人心的影響遠大於政治。哈維爾由異見人士當上總統,其才幹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但命運更是成功一大因素。哈維爾卸任總統後所撰寫的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憶述總統生涯,書中記載當總統的無聊事叫人會心微笑,全書滿是自我質疑,這是一般政治人物罕見的。哈維爾深明自己很幸運:「不僅美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把我視為童話故事的王子,我也經常覺得自己的命運很不可思議。」
昆德拉沒有哈維爾的運氣。法國《世界報》幾年前的一篇長篇引述認識昆德拉的歷史學家Pierre Nora說,昆德拉的命運從很多面看都是悲劇:為了繼續讓人聽見,他不能再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他被捷克人鄙視;諾貝爾獎忘記了他;連初時歡迎他的法國也漸漸不理會他。我懷疑昆德拉會否同意這論斷。他大概會認為,這樣輕盈的存在才是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