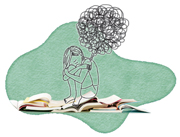【明報專訊】月初,在中文大學的畢業禮當天,有人在校園範圍內把有關青少年壓力的字句貼在身上。他寫下:「理想破滅」、「冇人傾訴」、「集體創傷」……呼籲學校和公衆關注。社運過後3年、疫情復常大半年,近期香港學生自殺個案急增,港大防止自殺中心統計,單在8至10月就有22宗,比去年同期翻倍。上周在立法會公布的最新一份《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亦顯示,近六分之一15至24歲青少年過去曾出現精神疾病,當中近四分之三卻沒有接受任何形式的專業協助。精神醫學系教授、醫生、資深社工和心理學家分別向記者表示,香港迫切需要更前瞻的措施;而解決方案不用外求,過去本港已有不錯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