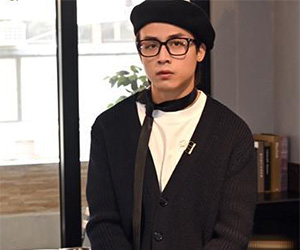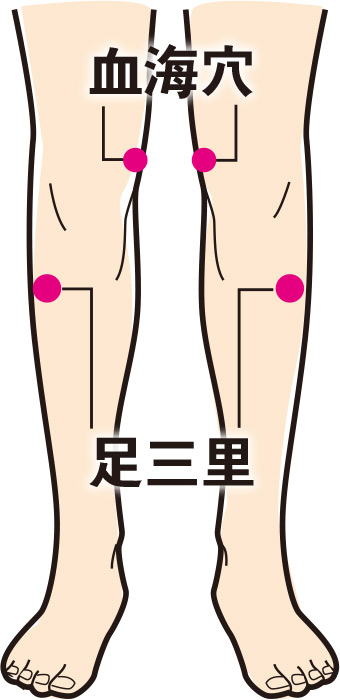【明報專訊】無人機劃破維港上空,時而砌成星河圖案、時而砌成《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預言會成為每月指定動作。無人機在藝術家Samuel Swope的巧手卻搖身一變,變成一根會飛的蕉、一個會飛的車胎。當藝術結合科技,容易着眼於科技炫目效果,反而忽略藝術本身,那根蕉、那個車胎意味什麼?
10多年前,香港有根蕉從超市出發,不疾不徐飛往金山郊野公園。它看起來跟一般香蕉無異,只是蕉頭蕉尾多了螺旋槳。平常是獼猴大哥來勢洶洶撲向香蕉,平生從未看過香蕉主動送上門,香蕉這番熱情倒嚇跑許多獼猴。突然,香蕉從天而墜,一頭獼猴率先試探倒地的蕉,但是剛才發生的事太匪夷所思,於是牠的腳步緩緩退卻;另一頭獼猴搶閘奔往,才發覺那是一根不能吃的蕉。
受動態藝術啟發 來港發展16年
飛蕉不是真蕉,而是飛行雕塑,它之所以能夠騙過獼猴,因為「蕉身」表面抹上真實香蕉的氣味,「真實和可能不真實之間存在着一種非常有趣的張力」,Swope坐在火炭工作室解釋BANANA MISSION: a monkey behavioral study(2010)。他比駿洋邨居民更早落戶火炭,10多年前從美國而來,跟畫家黎卓華合用工作室,靠一道木牆劃分工作區域,測試無人機時就不會影響她作畫。
Swope那邊有張長枱,案頭擱了電腦和零碎的電子零件,長枱旁放置車胎和一串飄浮的黑氣球,牆壁還掛上幾件作品。其中一個還在測試,形態模仿詹姆斯.韋布太空望遠鏡——太空望遠鏡窺探宇宙,但這件作品的鏡面不能直視自身,反從不同角度倒照自己的身影。地方不算大,還有足夠空間測試無人機嗎?他聞言笑道:「所有香港藝術家都面對相似問題,每個在香港的人都面對空間限制。但我嘗試積極一點,找方法在這個區域飛行。」正如他也從美國飛進香港藝術圈。
Swope本來在美國主修繪畫,後來授教雕塑的教授介紹動態藝術(kinetic art),作品塑造觀眾可感知的動態或從動態而來的效果,他受此啟發,開始結合藝術與科技創作。有年有機會來港交流,「我能感覺到這裏的藝術界即將發展得非常非常快,我想成為其中一員」,畢業後旋即執好行李、孭上背囊,飛奔香港開設工作室。16年過去,他發現香港藝術發展遠超他預期,也沒料到藝術與科技這一範疇那麼快成為顯學。
他以飛行和空氣為創作媒介,有別於傳統科學的使用方式,反而用在藝術裏探索不同議題。他沿藝術史追溯類似概念,時間回到1919年——《噴泉》(Fountain)尿兜面世兩年後,杜象(Marcel Duchamp)的《巴黎空氣 50cc》(50 cc of Paris Air)用玻璃瓶「盛載」巴黎的空氣,飛到美國送給贊助人。Swope解釋,我們大多時候都是無意識呼吸空氣,不會刻意感知空氣為實物,但是杜象透過這個概念塑造了空氣,賦予它可感知的體積,「我們可以感覺到它。因為它在容器內,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物體來對待」。
7秒射30紙飛機 上班族照上班
現在探討飛行和空氣,科技是不能跳過的路徑。2010年的飛蕉將無人機結合雕塑,無人機部分仍是現成;2012年起他開始自製作品用的硬件和軟件,第一個製造的作品是紙飛機發射器——7秒就能射出30架紙飛機,設計看似童趣,倒是成人社會的運作規律給他靈感,藝術試圖介入社會。
每個火炭平日的早晨,上班人潮從港鐵站出發,攀上大斜路,魚貫而入工業區,Swope形容似種「機械流程」。噠噠噠噠噠……頃刻滿天紙飛機劃破夏日長空,熱空氣賦予紙飛機翱翔天際的能力,好一會兒才降落人間。天上地下大量紙飛機,理應引起上班族的好奇心,佇足仰望才走回上班的路徑,「就像短暫停頓,或者暫時逃離我們的日常生活」。結果,無人理睬,紙飛機跟颱風一樣,打不亂香港人上班的節奏;唯一回應的是清潔工,火速到現場清理。Swope回想起《ta-ta-ta-ta-ta→》帶點歉意,記憶中還有一架紙飛機久久未掉下來,一直在空中飛行,「我們都被限制住,無法逃脫,但紙飛機做到了」。
紙飛機可能也算是一種飛行雕塑,後來Floating Room更見飛行雕塑的可能。在一個裝潢成家居的籠裏,放滿生活用品,它們突然飛起來,原來又是Swope的飛行雕塑。2016年在上海展出時,他先購買現成生活用品,然後加熱塑膠蓋在物件之上,最後抽取真空,得出物件形狀的塑膠,譬如垃圾桶、燈、鐘和鏡等;即使加上無人機,Swope改造它們發揮原有功能——發光、報時和反射,只是整個房間弄得一團糟,反思在自動化家居下,未來人類角色會否變成科技的照顧者,負責替科技充電和「執手尾」。Floating Room 2022年在美國華盛頓再次展出,用上數位製造技術(digital fabrication)製作。
今年2月的表演Nervous Thrasher有兩個新飛行雕塑——一個車胎和一串黑氣球。回看表演片段,車胎和黑氣球的動態和移動聲音酷似UFO,時而在觀眾面前游走,時而靠攏觀眾。Swope說表演參考美國B級恐怖片,透過速度和力量產生恐懼感。粗壯車胎的意象來自美國中西部文化中的肌肉車(muscle car),延伸至社會對未來科技的想像,「最終我們將擁有像飛行汽車這樣的空中交通工具,我們可以在其中移動」。我們又會否對未來科技恐懼,還未習得跟未來科技共處?
以聲音感知空氣 以「氣流」改變空間
車胎無人機由Swope操控,但觀眾事前並不知道氣球無人機由AI(人工智能)控制,經過訓練後會避開障礙物,如附近沒有障礙物,它就會四處飄浮。氣球擺動、扭曲的姿態怪異,當氣球靠近時,觀眾似是要跟其協商如何在同一空間共處,「變成了他們心中恐懼的問題,就像我需要移動,因為它離我很近」。無人機亦裝上感測器,讀取空間的數據差異,從而傳送資料至電腦即時合成聲音,然後放大振幅來播放音訊。現場喇叭播放合成的重低音,藉空氣傳播,透過聲音振動同時感知空氣。
另一方面,車胎無人機橫過造成大量空氣湍流,改變觀眾所感知的空間,但車胎並不是真實車胎,Swope遞車胎給記者秤重,「沒那麼輕,但也沒那麼重」。因為車胎只是他創作的雕塑,表面其實是黑色發泡膠,Swope雕刻成真實車胎胎面模樣;他在工作室用3D模型設計車胎支架,再傳到深圳工廠製造,最後自家加工。自製無人機需要平衡和微調數字,他先在工作室測試車胎無人機的平衡,數字穩定後才跑到南生圍測試飛行。Swope也參與表演,刻意不撿起車胎,只以滾動方式移動車胎,「如果我拿起它,它立刻就會表現出輕盈的感覺」。觀眾起初不信沉重的車胎會飛起來,但在超真實的處境倒會發生。
Swope用手在案上比劃出一條線,藝術跟科技可以壁壘分明,但「作為一個結合藝術與科技的藝術家,科技成為藝術媒介,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藝術家透過創意和想像力交錯藝術與科技,同時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他說:「不止是為了讓我們看到科技有多閃亮,而是為了更專注將藝術帶回我們身邊,也不是把科技帶到最前沿,然後藝術就變成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