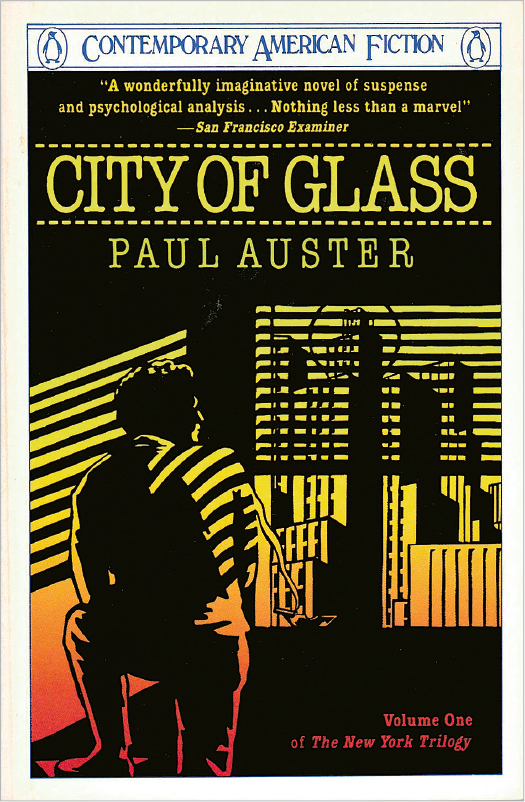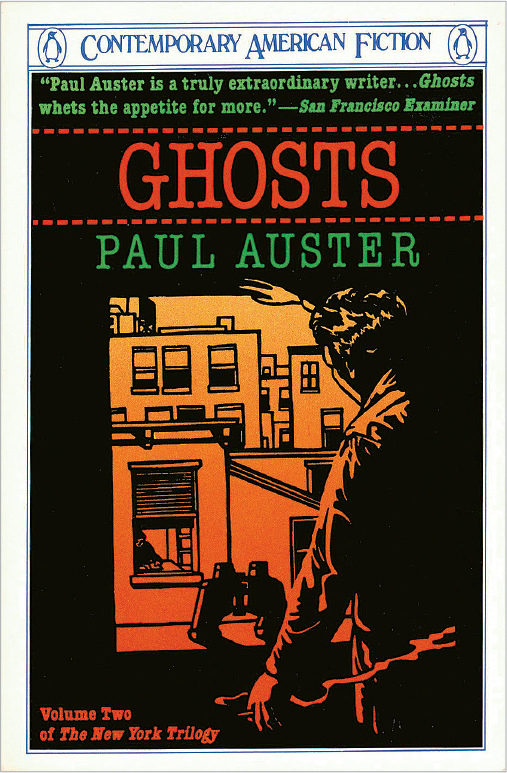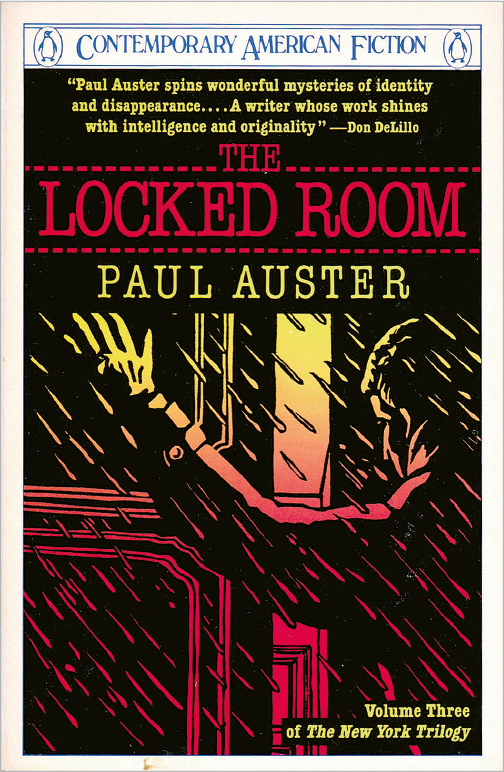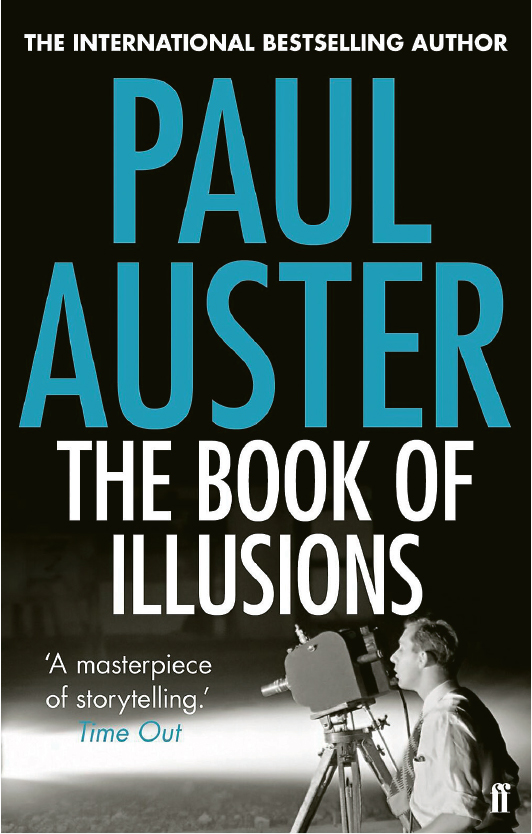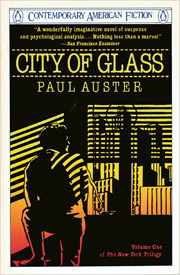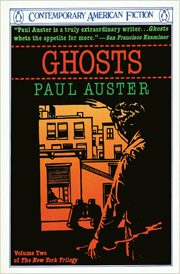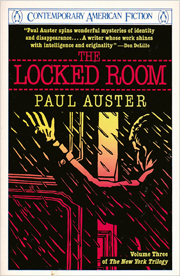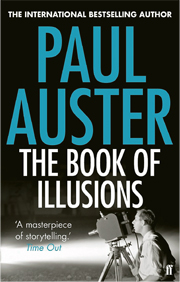【明報專訊】去年6月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逝世,今年4月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去世,美國文壇中堅又去一人。奧斯特是多面手,除了小說,他還寫詩、散文、回憶錄、自傳、評論、電影劇本、譯作(包括馬拉美、沙特、布朗肖)、傳記文學(如關於《鐵血雄師》(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作者克蘭的Burning Boy: The Life and Work of Stephen Crane),與柯慈(J. M. Coetzee)出版書信集《此刻》(Here and Now: Letters 2008-2011),又曾為美國華人導演王穎寫劇本《煙》(Smoke),二人更合導續篇《煙變奏之吐盡心中情》(Blue in the Face)。奧斯特的文學創作領域多元,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