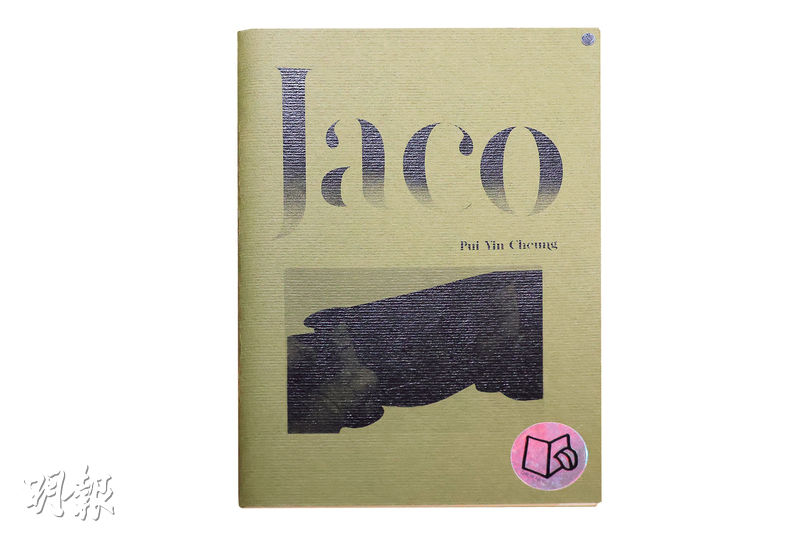【明報專訊】6月是同志驕傲月,記者翻閱專注酷兒敘事為主的流動閱讀平台「流動閱酷」共同創辦人彭倩幗(小彭)帶來的酷兒小誌,小彭說自己撰寫、編輯和整理,設計和出版的小誌,讓酷兒社群以微觀的角度,親自敍述自己的故事,「如果我要講好大聲、講好多東西,就要用一本書盛載,小誌則像是搭着肩,在你耳邊輕聲說,感覺較親切」,填補酷兒文化在公共空間的討論。記者這邊廂剛訪問完小彭,另一邊廂就收到一則新聞,指今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項目削減逾半,小彭和他身旁酷兒朋友Alex頓時嘆了一口氣。
圖書館閉架處理 催化另築平台發聲
酷兒(queer)是對所有非異性戀及非二元性別或跨性別認同的統稱。小彭的身分是男女以外的非二元性別,慣用的性別代名詞是「they/them」,他小時候不會主動參加本地同志組織的活動,「總覺得我好像不太fit in(適應)」,那時他覺得香港的同志社群以gay和lesbian為主,但他未能從這兩者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摸索自己的性別認同。2018年因接獲反同團體投訴,香港公共圖書館將10本涉LGBTQ內容的青年及兒童讀物閉架處理,小彭與友人便決定成立「流動閱酷」,「流動」一詞除了意味這閱讀平台非實體外,也代表性別流動。小彭提出疑問:「既然圖書館下了這個決定,閉架關於酷兒的書,是否同時代表圖書館這空間不接受酷兒出現?」
小彭認為出版是酷兒敍事、互相看見和連結的表達方式和媒介,當中小誌(zine)出版的創作門檻低,能繞過傳統出版的系統及制式,寄以作者最純粹的狀態及想法,這也避免了轉述或旁述時可能會出現只針對某些角度表述的問題。關於只針對某些角度表述的問題,Alex是印尼移工組織KOBUMI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他以媒體報道家務傭工為例解釋,稱「關於外傭的鏡頭只有虐兒、被虐和阻街」。那麼我們透過小誌能以什麼角度認識酷兒世界?
透過小誌了解其他國家酷兒社群
小彭說透過小誌可了解其他國家的酷兒社群。他讀小學時隨父母到泰國旅行,第一次接觸關於酷兒的書刊,「那時就是去看『人妖』show,入場觀眾可獲派一本catalogue(目錄冊),介紹表演項目和變裝演員」,小彭覺得很引人入勝。他熱愛閱讀,後來讀了不少酷兒作品,例如本地性別研究者沛然於2022年出版的小誌Jaco,名字取自一位2017年從港鐵大圍站平台躍下而亡的跨性別女士,沛然訪問了12名亞太裔跨性別人士,並寫下他或她們的故事。小彭說海外成長的亞裔酷兒往往來自觀念較保守的家庭,無論書中的他或她們是華人、越南人,還是泰國人,要公開出櫃或者確認自己的性別身分時,都面對同樣掙扎,「我要如何向家人交代?我有性別焦慮,想服藥,或者做相關手術(性別肯定手術或性別重置手術)時,該如何讓家人了解我的情况?」。
小彭說Jaco受訪者Phibi的故事讓他最深刻,Phibi的出生指定性別是男性,他(他們/她們,they/them)自我認同是一名泛性戀性別不一致(pansexual gender non-conforming)者。Phibi小時候第一次面對性別規範,是Phibi問能否與母親和姨媽一起塗指甲油,但Phibi被告知只能塗在腳甲上,並且不能被別人看到。Phibi也曾偷穿媽媽的女裝,直到參加高校的性別變裝日,才真正體驗一次公開變裝。Phibi說擁有跨越順性別(cisgender,即性別認同與出生時指定性別相同)或二元性別的性別認同,或令人感到可怕,感覺整個世界像要崩塌,對不墮入愛河、不結婚、不生小孩、被社交圈子拒絕和不能做某些需要法律文件證明的事情等,心存恐懼。
標籤反映社會取態 冀互相尊重
為什麼要分她、他、他們、她們、佢,佢哋?一些性別代名詞、性別認同和性傾向術語其實是方便酷兒群體向別人解釋身分。「就算我們不喜歡貼label(標籤),但當我們不清楚自己的性別或性傾向定位時,這些稱呼讓我們找到身分」,小彭說這些專有名詞就好比星座,人們未必迷信,但聽到自己星座的部分描述,會覺得與自己的性格頗相符。小彭認為討論性議題時所用的字眼反映社會怎樣理解酷兒,譬如說以前一般會以「人妖」和「變性人」稱呼跨性別人士,現在有了跨性別這說法,聽上去較為尊重。他認為由於性別流動,具體要用什麼稱呼,要視乎當事人怎樣形容自己,不過性別流動者現時反而沒那麼執著於「是否一定要確認自己是什麼」,將重點放在不同群體的互相尊重和接納。
提供一個安全空間 說出想法及疑問
記者問小彭,酷兒社群會出版小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否正因性別太流動,若要其他人代寫故事,未必能清晰表達?小彭認同這構成部分原因,同時人們意識到在Instagram或Facebook等平台,並非讓人長時間閱讀的空間,「在網上按鍵發文後,貼文即時觸及很多人」,印刷品如小誌的傳閱速度則相對慢,讀者則可以有多一點時間沉澱,思考創作者要表達的信息。小彭和Alex均說小誌或可為酷兒提供一個安全空間說出想法及對話,「可以是一個研究(investigation)、提議(suggestion)或想像(imagination)」,而且小誌能夠輕巧地對一些社會現象提出疑問「what if」。
表達想法的方式有很多種,近日上映的女同志電影《從今以後》將同志群體面對的問題放到大銀幕上,小彭說電影將議題「打入香港觀眾」,電影作為流動影像較容易閱讀和接觸觀眾。小彭亦留意到世界各地有不少以酷兒為主角的電影,似乎傾向放大主角從經歷掙扎,到真正成為自己,直接面對性別或性傾向認同的轉變,「如果我們不事先告訴觀眾,佢(主角)係跨性別者,其實佢每日生活跟一般人會否不一樣?會有好大分別嗎」。小彭說酷兒群體也會上班上學,也有普通人的情緒。而這種日常,小彭認為小誌較能述說,「因為小誌寫的是你個人故事」。
關注的人才明白 非同類人仍難觸及
不過小彭坦言酷兒圈子以外,社會對酷兒文化的討論是「總之你並非那類人,你很少接觸到」,正如酷兒小誌的讀者通常是與酷兒社群相關的人,「關注(酷兒)的人才會明白酷兒的想法」。那麼他們如何透過小誌連結彼此?小彭除了創立「流動閱酷」,也創辦了獨立小型出版社Small Tune Press,不時會到外地參加書展,每次都會帶上「流動閱酷」的藏書,包括小誌作展示,結識當地酷兒,認識其他國家的酷兒文化。有一本由居日的韓國男同志作家與攝影師合作的寫真集trailer zine,收錄不同國籍和性別的酷兒訪問及肖像,聚焦東京酷兒居住和工作的場景,小彭說「作者留意到新冠疫情除了影響民生,對酷兒社群也有很大傷害,例如從事表演或酒吧行業的性小眾,這本小誌以微觀角度審視其生活狀態」。
trailer zine的受訪者工種多樣,有go-go dancer(酒吧表演的舞者)、「牛郎」和變裝皇后等,「原來單是東京已有多元化的酷兒」,小彭說香港甚少有從事這些行業的酷兒討論。小彭最記得其中一名受訪跨性別男生Kila,Kila現在的外表陽剛帥氣,工作是幫女生美甲。Kila讀中學時發現自己與別人有些許不同,成年後接受荷爾蒙治療轉換性別氣質,母親沒有反對,中學畢業後應徵做婚禮生意的商店,面試時把頭髮剃了,Kila慶幸他的「頑童(brat)」形象沒影響他被錄取。trailer zine每一幀受訪者肖像的氛圍看起來很輕鬆,小彭從trailer zine受訪者的樣子從容看到出版物將創作者與受訪酷兒連結起來。
冀更多人認識及出版小誌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簡妙如於2021年發表了文章<醒醒吧!台灣龐克小誌及小誌文化政治>,簡教授引述紐約傳播學者Stephen Duncombe對小誌的定義,是「非商業、非專業、小規模流通的雜誌,由創造者自行生產、出版與發行」,獨立於傳統出版體制外的小誌被Duncombe視為另類具政治性的文化運動。「流動閱酷」前年應WMA邀請進行「尋溯我們:香港性/別小眾出版文化」駐場研究計劃,訪問了不同界別的小誌出版人士,探究香港同志歷史,最後將它們出版成冊,Alex便是其中一位訪談對象。Alex說酷兒在移民工裏佔一定人口比例,他的團體KOBUMI以往組織不少爭取移民工、少數族裔、女性和LGBTQ+社群權益的集會,並印刷集會道具,例如含反歧視標語的A4紙牌。Alex說除了KOBUMI,其他本地移民工組織一直有出版小誌的習慣,嘗試自白。小彭希望有多一點人認識並出版小誌,「流動閱酷」周六(29日)與香港逸東酒店合作,舉辦酷兒小誌市集,匯聚港澳台日英美和巴勒斯坦的獨立藝術家和出版商等。
「流動閱酷書誌交流市集」資料
地點:香港逸東酒店1樓Reception Lou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