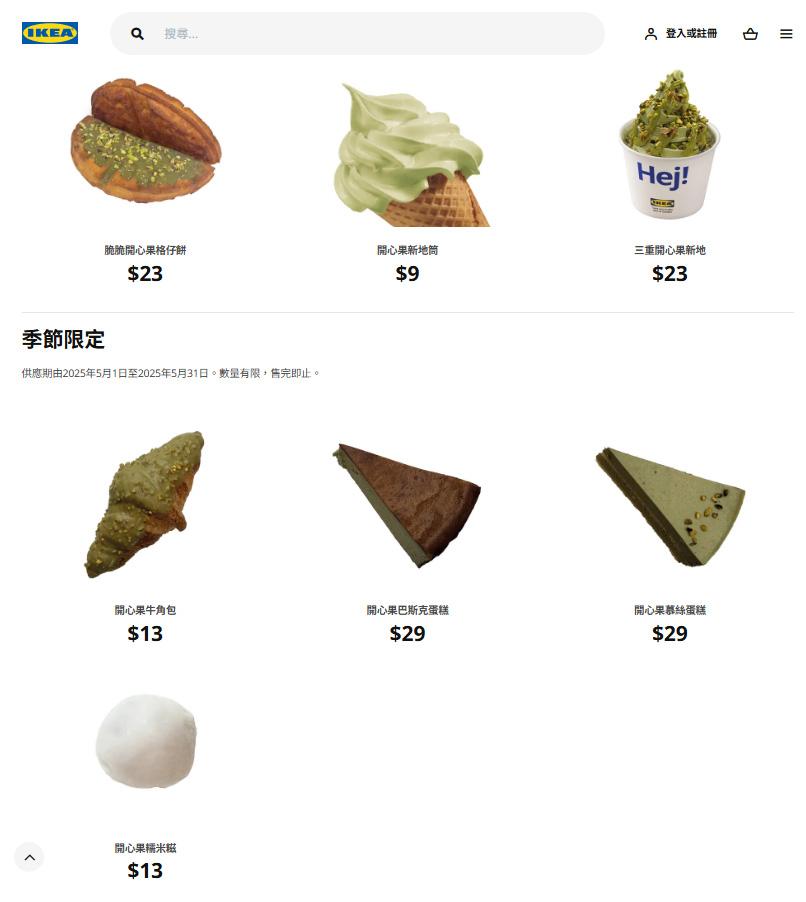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返了一個月美術館,其實夾埋返了50小時也不到,所謂度日如年就係咁。工作內容為撳𨋢、叫人排隊搭𨋢和嘟飛,和藝術一丁點關係都沒有。叫人排隊搭𨋢是一件很消耗能量的事,特別在外國人比例比日本人高的美術館,你很難給出一個令他們服氣的理由,為什麼必須從右邊排隊而不是左邊,以至為什麼要等美術館人員替你撳𨋢(連升降機內只去到3樓跟地下的兩個按鈕也要等人幫你撳)。
上班首天,我很自然地對排隊的外國人說英語時,一個鬼佬高舉雙手極盡浮誇地大聲說:「Thank God! Finally someone speaks English!」聽起來他受夠了連日來在東京語言不通,滿臉鄙視。若不是在上班,大概已經爆了鬼佬一鑊,所以只好哈哈乾笑兩聲。即便是2024年,大部分日本人還是很怕說英語,就算他們肯說也要花一番心思才能聽懂。平常彬彬有禮的supervisor一講英文便只懂大叫「NO! NO!」,有時會覺得那些一頭霧水的外國人無端受罪好可憐。
試過有一班俄羅斯的團體遊客來參觀,導遊是個操流利日文的俄羅斯女人。24張團體票全都在導遊的手機內,入場時必須逐個QR code開出來,即是要開24次。一班臉臭得不得了的俄羅斯人沐浴在美術館高級地段的晨光下,每嘟一個code導遊便粗聲粗氣地呼喝她的同胞進場;開到第8張票時,導遊臭着臉以流利日語大聲抱怨:「這太麻煩了(面倒臭いよこれ)。」日語環境裏,即使是客人,用上面倒臭い加不使用敬語,也是非常無禮的。某天到我站在嘟飛位,又再見到這名俄羅斯導遊。她已經知道即使跟日本人抱怨,也只會得到對不起的回應而不是特別待遇。所以在她以日文喃喃自語「麻煩死了」時,我回了她一句:對,我也覺得好麻煩呢。俄羅斯導遊嚇一嚇,然後用一個「看,我就說吧」的表情看着我。
做撳𨋢位時遇過一個印度女人,一打開𨋢門她手揗腳震地走出來,說是畏高。看畢展覽後,她深深吸一口氣,一邊催眠自己沒事才踏入𨋢門。想起跟一個同事閒聊,曾在法國專攻長笛吹奏的她回到日本,輾轉之下到公司旗下位於澀谷的觀光塔打工。以為她想做藝術相關工作才轉到這兒,她卻微笑着,說是在觀光塔被一個中學生一把扯過她的頭髮叫她幫忙拍照,扯到頸椎移位,公司才將她調到這邊嘟飛和撳𨋢。我大為震驚,忍不住問她大丈夫ですか?(沒問題嗎?)其實又怎可能沒事。同事笑笑,沒事了,繼續說她在法國時的快樂時光。
因氣流問題每次要按𨋢內的層數時,整張臉都會被風狂吹。被風吹得多會有皺紋,我也只得跟自己說大丈夫。站在揸𨋢位時太無聊,臨辭職前一段日子,我已練到能在𨋢門閉上的時候雙手交疊身體前開始鞠躬,一邊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多謝)直到門剛好閉上。苦中作樂大概是每個人不論處於哪個位置,都能生存的流儀。
文:Papaya Fung
(喜好是觀察人類 著有繪本touch和漫畫《地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