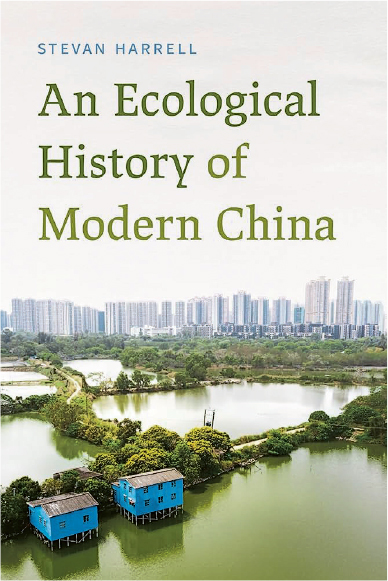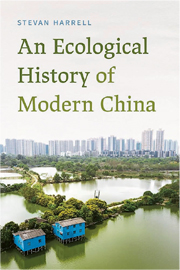【明報專訊】關於現代中國的歷史,一直以來都是論家必爭之地。不過回想起來,雖然論者或許各有立場,但大概都走不出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以人為中心的書寫角度。是故當我得悉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榮譽教授郝瑞(Prof. Stevan Harrell)教授出了本以生態角度書寫的當代中國史的著作時,馬上引起了我的興趣。
這本洋洋20萬字、500多頁的作品花了郝瑞教授近20年的時間來書寫,去年終於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郝瑞教授在書中從生態系統出發書寫當代中國史,於不同層次提出解讀的新框架與視角,讓讀者能從不一樣的角度回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因着對教授及這研究的好奇,我冒昧地約了他做了個線上訪談,了解了更多他書寫背後的思考,也無意中發現了他與香港的淵源。
s:郝瑞教授,你是如何參與到中國研究的?為什麼又會對生態史有興趣?
郝:1964年我念大學一年級時,學校有人來宿舍招募義工前往香港服務逃難到港的內地難民,我因此去了調景嶺,在慕德中學為難民教授了一個夏天的英語,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中華文化。回美國後我從原來的德文專業轉為中文專業,到碩士時我修讀了東亞研究,並立志以人類學為我日後發展的方向。後來我的博士研究則以當時的台北縣(現在屬新北市)為我的田野。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陸續開放給海外的學者去做研究,在一番思考與了解後,我在1980年代尾開始到中國西南部做研究。先是去了四川攀枝花, 後來又在涼山進行少數民族文化與族群的研究。
在涼山時我接觸到彝族(又稱諾蘇人),他們的生活仍然與土地非常密切,引起了我對人和自然環境關係的興趣。後來我幫自己學校發展一個以環境人類學為方向的博士班專班,進一步確定了我在環境人類學、對生態環境的興趣。
s:那對你來說,生態歷史與常規歷史有什麼分別呢?
郝: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問題,他們也會問生態歷史與環境歷史有什麼不一樣。我開始接觸環境科學時,既有一些和社會較相關的部分,也有和自然科學更接近的內容。當中我接觸到的韌性生態學(resilience ecology)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對我來說生態歷史就是採納了生態框架來寫歷史,把收集到的資料整合成相關的論題。帶着生態的視角、系統的視角,我們會發現很多時所謂前因後果(cause and effect)不是那麼的清楚的,因為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會相互影響。
可以說,生態歷史是綜合系統學的一個支學,也屬於環境歷史的一種。
s:你用生態歷史的框架來寫當代中國史,有收到不同的意見嗎?你怎麼回應?
郝:當然有的呀。比如談大躍進的歷史時,一些政治專業的學者會堅持說那是「政治掛帥」的年代,政治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我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同時我認為他們忽略了生態系統的因素,忽略了其他條件的限制以及其他因素對整個系統的反饋(feedback)與反作用力(reactions)。舉個例子,大躍進的不少政策其實邏輯上是說得過去的,像理論上只要農民把稻秧的株距縮減,在同一塊田裏插更多的秧苗,應該便能增加收成。但事實上這樣的想法忽略了農田裏其他的制約因素,導致了很大的災難。
生態系統不是機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生態系統裏的其他因素,在這意義下也有其主體性,人類不是唯一的行動主體。這是我這書很重視的一個觀點。
中國生態環境分區與歷史分段
s:你在書中把中國的生態環境分成了3個大區域,讓讀者更好的把握當代中國的生態歷史。你是如何劃分這些區域的呢?
郝:那劃分不是我獨創的,而是參考了其他地理、人文學者的想法。社會地理學家Joseph B.R. Whitney在其東亞地理的研究中提出,地形、氣候對人們的謀生方式有很大的影響。參照這些討論,我在書中便把中國的生態環境分成3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稱之「 China Proper」(註:可譯中國本部、中國本土、漢地等),這裏是挪用了歷史學及漢學的一個概念,指的是雨量充足、有足夠平地進行密集農業生產的地方,亦即包括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平原。其實從生態的角度,以上區域與台灣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同屬一個類別。
第二個區域則用了被另一位人類學家James C. Scott發揚光大的概念「Zomia」來命名,亦即指與東南亞相連的中國西南地區。那裏因為屬地形立體的山地而非平原地區,難以進行密集的農業耕作,農業剩餘相對少,過去不容易產生依賴農業剩餘支撐的統治階級,人口密度也遠較平原地區要低。
第三個區域則是連接中亞的西北地區。那裏雨量最少,除了一些綠洲外並不適合農業生產,人們的生活依賴畜牧業、有限的農業與貿易等。
目前共和國的國土源於大清帝國的疆土(但也有所變化),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自然的生態區域。認識到這些區域的差別,對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生態史很有幫助。
s:我也注意到你對共和國的歷史有不同的分段。比如你把大躍進後到1990年代末看作為同一階段,又把1998年看作重要的轉折點。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分段?
郝:我之所以會寫這本書,是因為2007年參與了一個學術會議,其主題是中國研究的新視角,當時我寫了一篇以生態角度去看歷史階段的論文,這本書便是從那裏擴展開來的。
大多數人寫共和國歷史時,會以毛時代及後毛時代來做劃分,並把毛時代分成文革前與文革兩個段落。其中文化大革命又是很多學者特別重視的時間段。這當然有它的道理在,比如文革時代那種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與實踐。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是因為書寫歷史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文革中最為吃虧,有把文革當作歷史中心來書寫的傾向。
如果從生態的角度,或從農民的角度,歷史階段的劃分會不會不一樣呢?
大躍進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當時把生態系統嚴重破壞了,造成了嚴重的人命損失。但走過大饑荒後,中國的生態狀况到1990年代其實差別不大。以農業作為例子,1960年代開始政府在農業上增加了投資。其中包括購買化肥、引進與建設自己的化肥廠;因為發現了更多的油田讓水泵得以普及,讓地下水得以更好被利用,擴大了灌溉面積;另外政府開始推廣「綠色革命」的品種(像水稻、小麥、玉米),而灌溉水的增加及化肥的使用讓這些品種擁有了生長的條件,並增加了全國的糧食產量。直到1990年代農業的情况還是比較類似,機械化要到很後期才開始提升,人力及牲口一直是主要的勞動力投入。在這意義下我覺得1960年代到1990年代在生態上是同一個時間段。
但我們也知道1990年代開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土壤、河流、湖泊的污染,森林退化、荒漠化等都愈來愈嚴重。1998年在長江中游、廣東及東北3個地方出現了大水災。然而當年的雨水雖然比較多,但並不是特別多,災情卻如此嚴重。人們、包括官員開始意識到經濟快速甚至無序的發展帶來的環境成本已愈來愈高,農村與城市的生態韌性已大大減少。
當時的知識分子、公眾對環境問題十分關注,當局為了自身的認受性(legitimacy)也不得不作出改變。我認為從當時起,中國政府的思路從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轉變成生態發展主義(eco-developmentalism),既要發展,但同時不能再置環境於不顧了。
因為這樣的轉變,中國從環境領域的落後國家,變成今天在很多方面的領先者了。比如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在大躍進時代是大概8%至10%,但在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則已到了23%,是非常大的成就。能源方面雖然因為總量的持續上升讓中國能源結構中較污染的能源仍然有所增加(像燃煤發電),但中國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首屈一指的。
發展、革命、科學概念 理解中國生態史
s:教授你在書中專門介紹了發展(development)、革命(revolution)、科學(science)幾個概念在理解中國生態歷史的重要性,可請你稍稍解釋一下原因嗎?
郝: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中講過,「發展才是硬道理」,說明了「發展」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性。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共和國,發展、經濟發展、富國強兵一直是當政者的核心追求。
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毛時代的中國講革命,後毛時代的中國才講發展,我並不同意這觀點。革命其實是發展的手段而已,後來革命已讓位於改革,在講法上有所變化,也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由於革命、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等始終是中國政府的理論來源,不能放棄,故上述變化也創造了一些理論上的困境。
科學則更有意思了,但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在簡短的訪問中講清楚。馬克思主義與科學本身便有難以辨清的糾纏關係,比如馬克思便自認為是在利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社會。而科學有時指其獲取知識的方法,有時則指涉物質世界的內容。在當代中國歷史上我們也能看到科學知識與政治會出現矛盾,比如像社會主義時代就專業(白)與革命(紅)的爭論。科學的專業知識與革命中強調的群眾路線也會有衝突,專家學者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始終有某種張力在。近年政府官員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日益強調科學知識的重要性等,科學成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也反映了科學是其認受性的來源。
在這意義下,我認為「發展、革命、科學」這一組概念為我們提供很有效的視框去解讀、解釋不同時代的政策與政府行為,也讓我們更好的把握當代中國的生態歷史。
s:在你看來,未來的中國生態狀况,存在哪些挑戰呢?
郝:正如我在書的結論強調,一個系統是否有韌性,可能只可以作事後總結,故現在要我作出預測其實有些挑戰(笑)。
總體來說我覺得目前全球的人口太多了,1947年我出生時全球人口才20億,現在已經是80億了。長遠來說地球無法養活那麼多人口。中國的人口最近宣布見頂,對經濟學家來說可能是個大問題,確實短期內或許會引起些社會問題。但長遠來說,地球的人口減少其實是件好事,而中國未來將會帶領全球在人口與環境中尋找新的平衡點。
中國領導層對像能源、糧食安全的焦慮,可能會影響到人類與環境的平衡。我覺得有些焦慮是不必要的,像中國的食物產糧一直在增加,所生產的熱量早已能養活中國的人口。
在我的研究裏看來,政治體制對環境治理沒有太大影響,國家間在環境領域表現的差別主要視乎工業化與經濟現代化的程度。中國有些問題比較棘手,像土壤污染、湖泊的富營養化等,但有些方面則已做得不錯,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雖然做得不夠快(但各國都不夠快),卻已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了。
s:最後,因着這書你有什麼想跟香港說的嗎?
郝:我上一次來香港已經是2018年了,但每次來都覺得這裏很有意思。我知道這幾年香港有不少變化,中間也有讓我失望的地方。但我每當想起香港,都會記起這裏是讓我打開到亞洲的窗口,心中總是有股溫暖、想愛護這地方的感覺。
香港作為人口密度那麼高的城市,一定要好好保持一些開放的空間與綠地。香港有不少山與島嶼,市民也很愛惜這些郊野的地方,在生態保護上有一定基礎。至於執政者有沒有這樣的自覺性,我因太久沒有來過,着實不太把握情况了。
後記:郝瑞教授早已過了古稀之年,但在線上聊起來仍然中氣十足、聲如洪鐘。得悉他早年曾在調景嶺教英文的事迹讓我十分意外,身在太平洋彼岸的他突然用廣東話跟我聊了兩句,大大增加了我對他的親切感。
我拿到書本時覺得封面特別面善,總覺得是天水圍的景色,但書中卻沒有提及封面照的來源。訪問時忍不住問了教授一下,原來出版社在公開的圖庫找到這張照片,郝瑞教授覺得拍得很美,雖然書中內容沒有談及香港的部分,但他問了一些香港友人,大家都對他這書選用來自香港的照片表示很歡迎,他便也同意了出版社這安排了。
在談到生態歷史的書寫時,郝瑞教授在書中引用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自然保育先鋒John Muir的說法說——Ecological history deals with how “[a thing] is hitched to everything else in the universe”。大概這書的封面用了天水圍的照片也是這句說話的印證,而讀者自然也能從書中找到文本和自己、自己與自然環境裏其他元素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