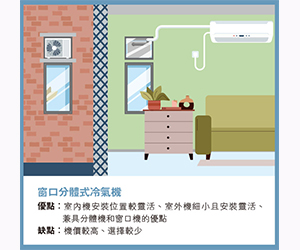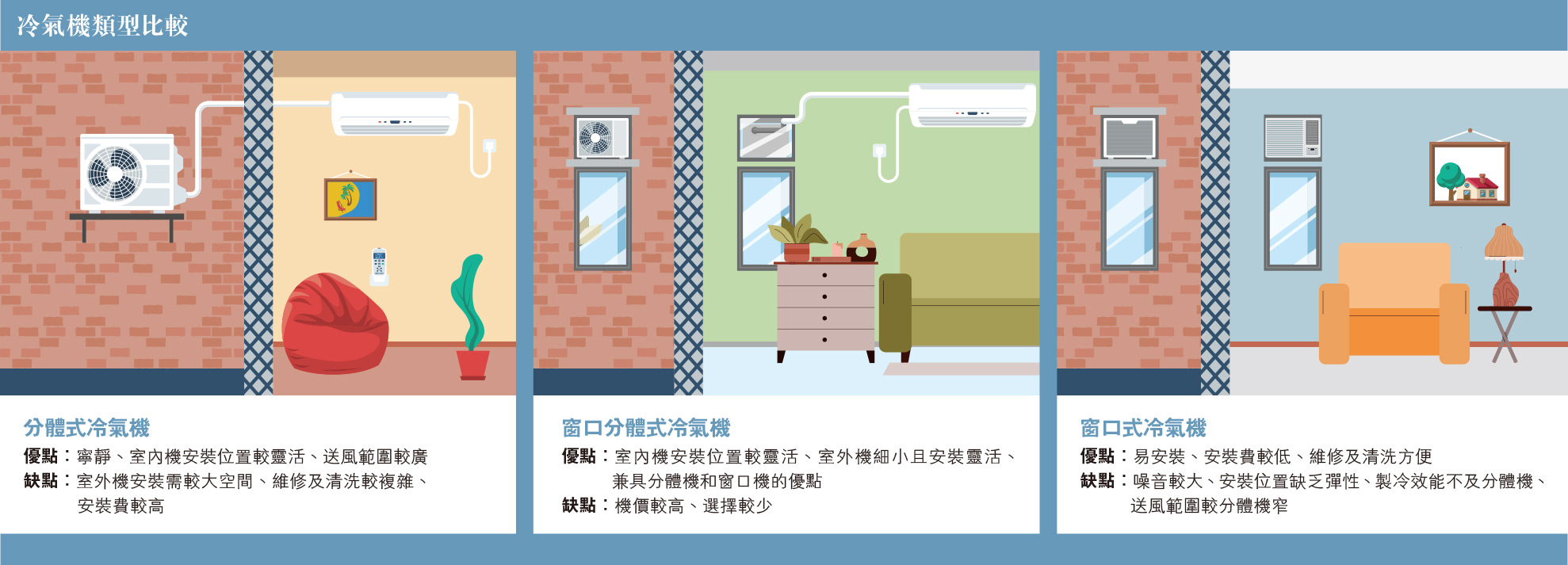【明報專訊】扎根本地多年的「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歷經去年主辦機構高層人事變動,低調舉行第29屆後便沉寂下來。今年9月以電郵通知「尊貴朋友」活動將暫時停辦(take a brief hiatus),看似為30年路途畫上休止符(如果不是句號)。今期《開眼》邀得藝評人馮美華與3名ifva不同時代的靈魂人物一齊對談。看看在他們眼中,ifva的暫歇到底意味着什麼。
以下是由記者整理的對話錄。
蔡:蔡甘銓(Jimmy) 林:林淑儀(Connie)
鄺:鄺珮詩(Teresa) 馮:馮美華(May)
馮:可否請3位介紹一下自己和ifva的淵源?
蔡:1990年代我在香港藝術中心擔任電影節目部主管,創辦了最初ifva的評審機制、比賽組別及媒體中心等「基礎建設」。
林:我在1997年加入香港藝術中心,負責管理盛智文媒體中心,透過舉辦工作坊、入中學推廣錄像及提供器材支援ifva的發展;成為香港藝術中心的節目總監後,也在早期兼任過一年電影及錄像部經理,一直有幫助發行ifva得獎短片,後來便擔任了藝術中心總幹事。
鄺:我在1997年6月短暫加入過第3屆ifva,離開不久後Jimmy又找我擔任電影及錄像部助理經理。5年後為了解電影的可能又到英國留學一年半,然後2004年回來接手ifva總監,一做就是10年。直至2014年接任藝術中心節目總監後,ifva就交給了Kattie(范可琪,2015至2022時任ifva總監)。
繼承獨立短片比賽 主流之外自由表達
馮:Jimmy,為何一開始你會舉辦ifva?
蔡:說來話長,ifva的前身有兩個,一是市政局的「香港獨立短片比賽」,另一個是藝術中心的「香港自主錄像比賽」,最終在1995年合併為「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1999年隨着市政局取消,便由康文署接手,和我們合作。當時創辦的原因有三,首先是繼承火鳥電影會、衛影會每年一度獨立短片比賽的傳統;其次是發現年輕人比起書寫更喜歡拍攝,所以想推動他們更自由地表達自己;最後是當時主流電影強勢,便想舉辦一個强調創作盡量不受主流影視、經濟、政治影響的比賽,希望參加者「自己作主」,不過合併後便以「獨立」為名。
馮:合辦期間誰佔主導?參賽影片質素如何?
蔡:合併前後政府都有提供資助,亦未有干涉。不過早期參賽短片較受主流影視影響,但評審多為非主流的電影人,第2屆經理周強又提出公開評審會議紀錄,往後的參賽作品也就愈來愈「獨立」。
馮:那當時揀選評審會否有特定的傾向?
蔡:當時我們規定每組最少要有5個評審,而當中最多只能有兩名同電影有關——電影不可以完全由電影美學主導,它應該更多姿多彩,從人文學、文化研究及其他藝術範疇等角度或可看到更多。
林淑儀亦在此時加入香港藝術中心,在盛智文媒體中心透過提供剪接機器,與開設剪接工作坊推廣影像普及化,並邀請ifva得獎者執導。適逢時任特首董建華推出「資訊新紀元」政策,ifva又在第3屆增設青少年組,她便在SONY資助下走入校園——由提供器材到就業機會,ifva一邊培育新人才,一邊支持創作者生存下去,累積了一批當今知名導演——黃修平、黃精甫、彭浩翔,甚至還有內地名導演賈樟柯。而由開初的6個組別簡化為公開組、青少年組及動畫組後,加上後來的亞洲新力量組,如今的ifva逐漸成形。
緊貼時代 孵化多元項目
租借器材、舉辦工作坊的媒體中心,漸漸成為ifva參加者的「打躉」之地,亦是相互取經的問診室。在鄺珮詩主理下,ifva亦對參加者的支援進一步拓展到比賽後的發展,把作品帶往國際的同時,也以影像走進本地不同社群。
馮:Teresa,你任內10年間ifva又有何改變?
鄺:我任內主要做了3件事:擴闊對媒體的理解、加強文化交流、拓展對參與者的支援。當年負笈而歸時,我覺得ifva是一種精神,而比賽只是形式,便「以媒體作為工具鼓勵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為核心擴張ifva的媒體光譜。故第10屆ifva節除了放映得獎作外,亦開始加入聲音影像表演、國際藝術交流,也找來學者在出版物討論媒體的未來;第11屆則在比賽加入了「單熒幕互動媒體組」,即如今的「媒體藝術組」。同時也在2010年開設了CINEMA 2.0本地媒體藝術展覽,而ifva終也在第17屆更名為Incubator for Film & Visual media in Asia(原名Hong Kong Independent Short Film & Video Awards)。
馮:即你把在外地留學的啟發帶了回來?
鄺:可以這樣說。因在英國回來後YouTube開始普及,不同機構都想用「微電影」等新方式宣傳,我們便在2006至2012年舉辦了ifva greenlab短片委約計劃,為港鐵、Google等委託方與ifva得獎者雙方牽線,提供更多創作機會。為了延續這種與Alumni(得獎者)的關係與社群,每年也會邀請他們設計主視覺、擔任評審,同時也繼續思考可以如何支援中、新生代創作者,例如首部劇情片後如何孵化下套電影等。
林:對,往屆得獎者曾翠珊奪得金像獎最佳新進導演獎的《大藍湖》,雖是獨立製作,但我們亦有協助其監製、發行。
鄺:當時她寫了劇本卻不知如何拍出來,後來我們提供了人手剪接、製片、轉製菲林等,其後幫忙聯絡高先電影發行。此次嘗試之後,我們也支援了不同得獎者的創作,例如支援江記(江康泉)《離騷幻覺》的部分片段。適逢我任內不同國際電影節陸續冒出,我們便帶了不少得獎作到海外展出,ifva亦漸為外國創作圈認識,Connie也曾受邀到德國奧伯豪森電影節、巴塞隆拿亞洲電影節任評審。
馮:發展過程中有否遇到困難?
林:當初面對資助不斷縮減,幸好同事都覺得ifva很重要,願意撥調一點資源,才讓它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鄺:不過因為ifva比賽始終難覓贊助,而ifva節的資助亦不足應付比賽的開支,所以促使我們不斷生出greenlab這樣的「小細胞」自負盈虧。始於2009年的另一小細胞「影像無國界」 則可謂是奇蹟,一個為香港少數族裔青年而設的影像工作坊,如今竟成了日本學術界的研究對象。
林:ifva停辦,我最擔心的也是「影像無國界」。媒介無分種族,在乎有無接觸的機會——少數族裔並非「要人幫」,但卻較難得到資源。雖然社福界後來也有類似活動,但藝術中心始終對錄像與放映更有經驗,而ifva得獎者亦會到學校作前線教育。當時發現有參加者竟從未到過灣仔,所以可藉此放映帶他們外出。了解他們更多之餘,過程中也讓他們建立身分認同,同時獲得一技之長,例如《手捲煙》的主演Bipin便曾經是參加者,更有參加者開設了婚姻攝影公司。
鄺珮詩轉任其他職務後,ifva總監一職由范可琪接任,其間籌辦了較貼地的「賽馬會ifva Everywhere影像嘉年華」,推廣媒體藝術,後來更在第28屆首辦精選各地佳作的「VR影院」。而林淑儀表示推廣的工作其實是在跌撞中開展,後來再逐漸開源,幸而本地媒體藝術進步神速,如今放諸國際都毫不失禮。由主辦比賽到為得獎者發展分憂,ifva在香港深耕之餘,也漸受國際認可。但暫停過後,又會是如何?
沒門檻的練功場 支援生態難以取代
馮:ifva已不止是栽培creator,而是幫助他們發展career。現在雖有不少網上平台讓年輕人發布短片,但是否代表ifva可以就此消失?
鄺:環顧亞洲,同時包攬短片、動畫與媒體藝術的,除了2022年後音訊暫無的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祭,就只有ifva。但這次停辦可惜之處在於,竟是主辦方本身提出。2023 年離任前我們便被告知ifva曝光不足、不值得投資,但即使邀請主辦方高層出席頒獎禮、陳說得獎者成就,亦徒勞無功。
蔡:比賽,或許可以重辦——但背後的配套、支援等一整個生態則難以取代。歷經29年,ifva早已由香港藝術中心的私人節目,變為香港所有電影愛好者的共同資產。下決定時不應只是通知,而是要廣泛地諮詢,每屆千多名參賽者的希望一下落空,他們可以到哪裏去?
鄺:事實上他們曾聯絡我,卻未有找過Kattie和Connie。既然願意繼續ifva,會否可以開放討論未來續辦的形式?
馮:但如今ifva停辦已成定局,基於你們過去的經驗,這種停頓意味着什麼?若早10年停辦,又會否有所不同?年輕人是否更難開始拍攝?
林:以前我曾說「ifva唔可以唔做」,因為它不止關乎香港藝術中心,而是影響着影像相關行業的整體發展。因為ifva是一個沒有門檻的「練功場」,能讓有天賦卻無電影背景的人被看見,也容許創作者「埋班」拍出完整作品的部分內容,成為日後申請資助或參加其他比賽的樣本。而坊間難以獲得的資訊,參加比賽後也會找到合適的諮詢對象。所以電影界不會因失去ifva而死,但絕對會因此失去了好多活力和新力量。而如果創意產業裏沒有容許新嘗試的空間,創意又可以在何處釋放?不過我相信縱然因為ifva停頓失去了資源充足的網絡與平台,但有熱情的年輕人一定會有方法繼續前行,只不過會比之前辛苦。
鄺:年輕人會否更難開始拍攝,我會說「是,也不是。」因為鮮浪潮等比賽都要求參加者是電影工作者,ifva卻是一個「幼稚園到老人家都可以參加」的比賽。但現在還有YouTube等平台,世界不會因此停頓,只是可能少了一個推你踏出第一步的契機。第10屆拍宣傳片時,黃修平說過「香港勝在有ifva」,如今可以說「香港勝在曾經有過ifva」。雖然ifva的停辦令人憤怒與可惜,但也欣慰它曾陪伴不少電影人成長。於風華正茂時結束,未必是壞事,因為我相信ifva的細胞會繼續以另一個形式存在,不會消失。
蔡:我發現2014年後碰見的年輕人已經和以前不一樣——「唔做呢啲,咪做嗰啲,只是有個大機構會讓一切變得更方便、有更多資源。」
ifva至今孕育了無數本地電影製作人,歷屆參賽者和評審代代相哺,對他們來說,ifva停頓,遠不止是失去一個發布平台這麼簡單。日前,由獨立電影人成立的電影發行商「影意志影院」宣布已於去年解散,惟曾是ifva得獎者、現移居台灣的前藝術總監崔允信以同名社交專頁宣布舉辦「獨立短片大獎2025」。或許那些流着ifva因子的細胞,確實尚未消亡,會在花果飄零之際接過曾經的薪火,讓下一批影像匠人繼續發光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