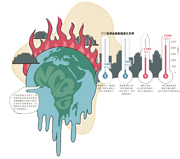【明報專訊】瓊瑤在家中去世,留下千字遺書和一首詩。我這一代的人,如果年輕時親近文藝,一定看過她的愛情小說。中年看電視劇《還珠格格》,很喜歡,見到原著出自瓊瑤,心想她的創作上了一層樓。沒有想到,最後會被她的遺詩〈當雪花飄落〉感動,特別是結尾:「當此刻…當此刻… /有如雪花與火花同時綻放 /我將飛向可以起舞的星河」。然後從前醫生專業的理性反應就出來了。她是自己結束生命,遺書娓娓道出想法:「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她要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雖然她好意提醒年輕人,這樣的死亡方式,是在她生命的終站的決定,「年輕的你們,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一時的挫折打擊,可能是美好生命中的『磨練』……」,但是畢竟「自殺」是要防止的,「安樂死」也不是社會可以輕易打開的議題。她這樣走了,我們要怎樣(理性地)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