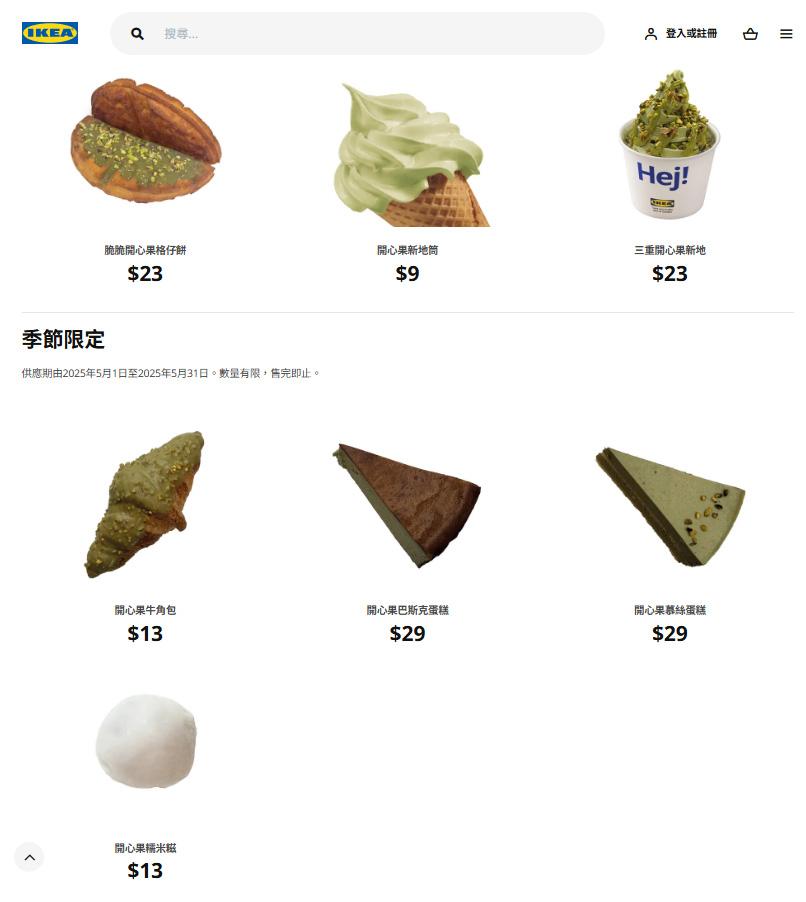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航拍下的新界東北是一片片魚塘,而咫尺之間,對岸的深圳是一幢幢摩天大廈,「包圍古洞的山和魚塘真的很迷人,古洞地方開揚,又多平地,能吸收大量陽光,很適合曬豉油和耕作。」這句話來自法國的藝術家Daphne Mandel,她與搭擋加拿大裔攝影師Guy Bertrand一起拍攝了古洞鄉村紀錄片《茶粿》。發展局上周表示,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餘下階段的首批受影響住戶,須於5月起分批遷出。古洞未來不知會成什麼樣子,但我們可從《茶粿》重溫古洞的此時此刻。
探索香港新舊過渡地帶 被古洞人事吸引
Daphne原在法國凡爾賽讀建築和城市規劃,是一名園境師,她於2008年來港工作,本身打算重操舊業,但很快便發現行不通。作為園境師,她游走在香港市區,觀察到高樓和樹「超級密集地」共存,「就像有兩種力量在拉扯」。假如走上太平山頂或其他高處,俯瞰市區任何一幢建築,Daphne覺得那景觀並不美,「我可以說巴黎每一幢建築單獨來看都很漂亮」。但若從藝術角度,把香港那些高樓和樹木當作兩個色塊來看,她卻感覺很有趣。
香港與法國的城市規劃顯然不同,Daphne指法國的城市與大自然完全融合,香港的野生環境卻是「一層又一層人工的自然,那完全受人類操縱」。譬如說路邊斜坡鑿了不少排水孔,「這讓我難以置信,它不是一座山,而是有排水系統的混凝土塊,但它被樹覆蓋」。Guy笑言香港的城市景觀也與加拿大不太一樣,他的家鄉滿地可是一個建築「橫向發展」的城市,非常靠近自然環境。當Guy於20多年前來港,飛機在舊啟德機場降落,他被香港這垂直建樓的城市驚呆,「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物」。
作為要從環境中尋找視覺刺激的攝影師,Guy很快發掘到香港街道獨有的新舊對比——摩登高樓與唐樓。Guy從唐樓中觀察到1950至1960年代的香港建築美學,「特定物料的選擇和建築結構顯現那個年代獨有的強烈特色」。然而Daphne卻在新界鄉村發現香港的另一面——水平線一字排開的房子,家家戶戶窗門大開,閒時與左鄰右里寒暄幾句,「一切似乎距離我們在港島的生活很遠,(我們的社區)較為分離」,她說。
Daphne居港17年,她一直花時間探索香港,尤其是既不屬於鄉郊,亦不屬於市區的邊緣地帶和廢墟,「我對(市區與郊區之間的)過渡地很感興趣」,因為身處這些邊緣地帶可見「新與舊、歷史與當代,以及失修棄置與精緻打理的事物之分別」。2019年,Daphne與會講廣東話的友人到訪毗鄰港深邊境的上水鄉村「古洞」,當時年逾90歲、村民人人稱呼作「婆婆」的賴運珍主動邀請她們到家中作客。好客的婆婆與她們分享古洞人事,吸引Daphne數年間不斷重遊舊地。
從茶粿看見「跨代共鳴」
鏡頭全部原汁原味
Daphne從婆婆口中得知古洞的農業和工業發展故事,而這鄉村部分土地隨北部都會區發展,未來將沙塵滾滾。「我和Guy希望透過紀錄片去描繪古洞的獨特,同時述說這裏將發生的事情之普遍,即城市化發展令某些(鄉村)生活模式消失」,Daphne說香港以外,世界各地都將鄉村發展成市鎮,「我們認為這紀錄片也能引起外國人共鳴」。「我們不想製作一齣看起來只是懷舊、回望過去的電影」,Guy續說,沒有預設的場景、服裝和訪問問題,《茶粿》所有鏡頭都是原汁原味,「當然我們有做剪接來縮減影片內容,使其節奏更緊湊」。
既然是古洞紀錄片,為何片名會叫茶粿?原來生於廣東的婆婆是客家人,她不時會做茶粿給Daphne和Guy吃。有一天,Daphne和Guy探完婆婆,他們在古洞其他人家看到一個極大的蒸爐,「就像放置文件的抽屜」,望見火焰燃燒,水蒸汽正在蒸煮鋼盤上的茶粿,Guy和Daphne不禁思考茶粿對村民的意義。茶粿的做法不盡相同,「茶粿總是人手製作的,各人有與別不同的食譜」,他們後來聽說茶粿是客家人慶祝節日時款待他人的傳統食物,「這是跨越世代的家庭聚會中都會分享的食物,似乎與我們紀錄片敘述的主題有關,同樣關於一些跨代共享的事物」,Daphne說,《茶粿》由此得名。
不過Daphne所說的「跨代共享的事物」到底是什麼?或許是人生觀——保持謙虛、腳踏實地做事,Daphne說這是她和Guy從古洞村民學到的精神。例如婆婆3歲時被父母賣給別人,那時「賣到40元、10斤魚、10斤肉和兩埕酒」;30歲定居香港,但香港丈夫是船員,出海歸期不定,一家人聚少離多,她邊工作邊獨自撫養5個子女。「婆婆渡過重重難關,她辛勞地工作、買下自己的房子,成功創造幸福的生活」,Daphne說婆婆與其他村民一樣堅韌,見過大小風浪後變得強大。儘管子女成家立室、搬離古洞,婆婆仍然樂觀,說隔籬鄰舍會找她打牙骱,去社區中心又有活動參加,她一個人也不無聊。
記錄建構香港的人
除了婆婆這樣好客之人,古洞還有建構香港的人。紀錄片開首訪問了古洞磚廠「中華玻璃纖維製品有限公司」創辦人歐次鴻,歐次鴻特別研製用於承托和固定鋼筋的「蝴蝶磚」聞名香港。原來搭建各區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和青馬大橋的石屎磚,也出自歐次鴻的手筆。Daphne形容歐次鴻的手作品雖然「小眾」,但其蹤影遍佈香港,「它分散在我們的腳下、天花板上、地基上,它無處不在」。
影片中72歲的歐次鴻頭髮花白卻沒顯老態,他說這是因為他的腦袋一直在思考,勇於嘗試新事物,「唔諗就好快衰老」。世界在進步,潮流在更迭,「你無法改變(潮流),無論是什麼身分,不跟時代變便會落後」。
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下,志記鎅木廠幾歷搬遷。3年前記者曾訪問志記第二代東主王鴻權,那時志記身處新界東北發展範圍內的馬草壟,須清場搬遷,後來覓得新址續命。王鴻權一直強調要「尊重木材」,以及愛護大自然。去年Daphne和Guy拍攝《茶粿》,訪問王鴻權,他依舊如此,「他告訴我們大自然與他的連結,還有他的木工藝品背後的意義」,Guy說。Daphne則從王鴻權滔滔不絕的分享中,感受到王對其事業「一生的承諾和奉獻」,以及如何用相同材料,順應經濟轉型和時代變化來「重新發明另一種使用它的方式」。例如1997年後原木大減,王回收木材循環再用。這種對事業的投入不是歐次鴻和王鴻權獨有,年輕一代像悅和醬園第三代傳人龐中衡(Jack)亦如是。Guy說龐中衡掌握香港流行文化的脈絡,利用社交媒體與年輕人交流,以時下的meme或潮語引起共鳴,在不改變傳統的情况下推動人們對悅和醬園的關注。
這樣看來市區和鄉郊其實從沒分隔很遠。又譬如古洞的農民,他們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生活節奏與城市人大相逕庭,但市區街市賣的蔬果或是他們的勞動成果,他們與城市有緊密的連結。農民晏富琴在紀錄片中憶述,她2002年從重慶遠嫁香港丈夫,兩夫婦一起經營農場,起初養豬種菜,後來政府推行《豬隻飼養工作守則》,加強對農場的排污規管,她們一家便沒再養豬,轉而種植幾乎一年四季都有收成的火龍果,冬天還會種當造的士多啤梨。即使沒晏富琴家大的農場,Daphne說古洞村民每家每戶幾乎都有塊種菜小田。Daphne笑言她每次探訪住在古洞40多年的彭貞,彭貞不是在摘黑莓,就是在搾果汁,總是送吃的喝的給Daphne和Guy,「那些都是從泥土裏新鮮採摘的食物」。
建立信任 拍出四季變化
Daphne和Guy與攝製隊拍攝《茶粿》逾50日,但他們實際用了1年多時間與村民交談並建立信任,還有拍出四季變化,「四季的元素很重要,尤其農民在每個季節有不同產品,他們在各季節講的故事便會有分別,討論的氣氛也不一樣」。Guy續說古洞村對他和Daphne十分熱情,亦對其紀錄片計劃感好奇,大伙兒很快就熟稔起來。
去年一眾古洞村民去了《茶粿》在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的首映,Daphne從村民的臉容看到各種濃烈情緒,「有些人受感動,有些在傻笑,有各樣複雜的情緒」。Daphne說村民是她們重要的人,她和Guy都希望村民喜歡《茶粿》。Daphne記得當影片放映完畢,村民走上台,台下全是掌聲,「我們不是為紀錄片鼓掌,而是為村民的故事鼓掌」。《茶粿》目前只會有限度公映,沒有在商業戲院放映,Daphne說她們仍在探尋讓公眾更容易觀賞紀錄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