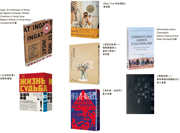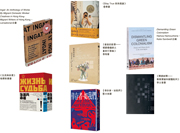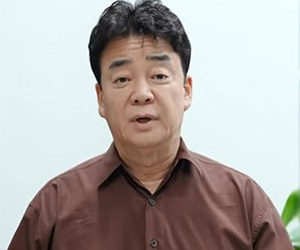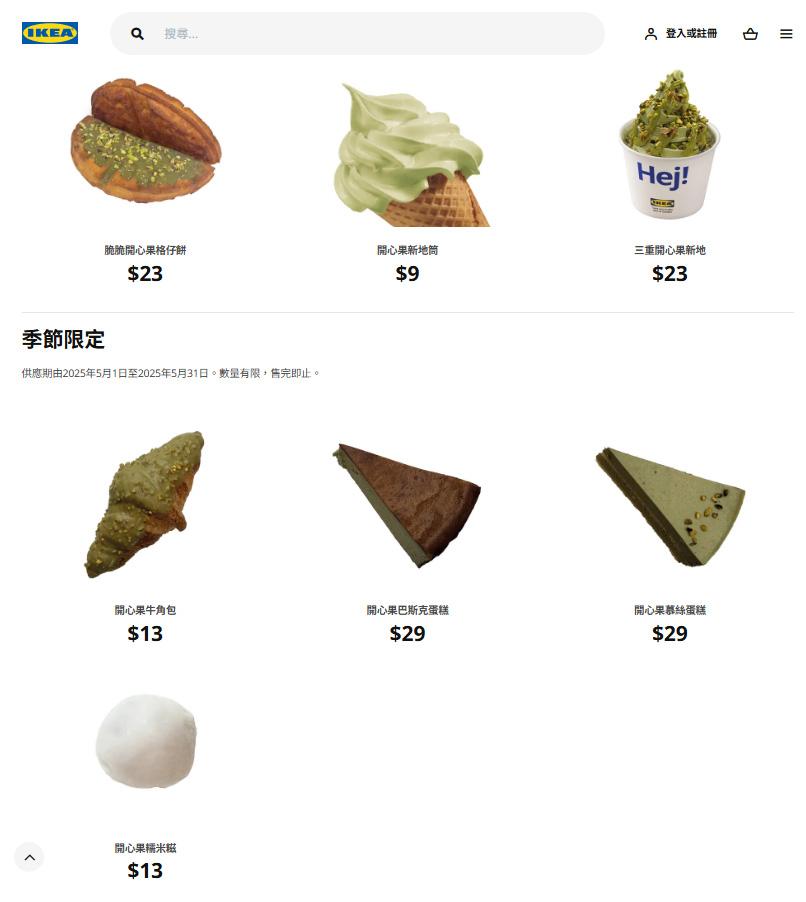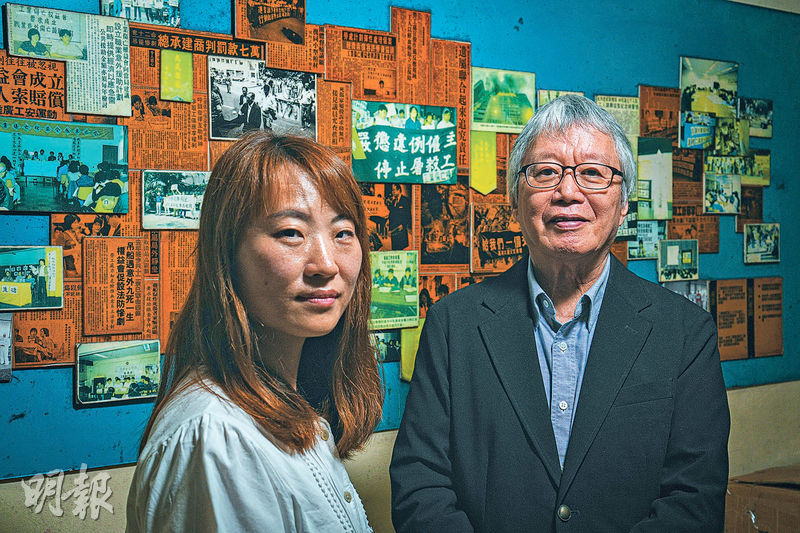【明報專訊】不算是試當真的忠實fans,但上星期讀到他們10月結束的消息,仍覺傷感。後來與上萬觀眾一同從直播看到游學修、蘇致豪(蘇豪)、許賢穿上招牌西裝(及拖鞋),認真解釋結束主因是創作人身心俱疲,作為觀眾,釋懷以外,感慨依然。
對香港大眾來說,一個YouTube channel畫上句號,其實沒什麼大不了。流行文化能量大、輻射廣,周期短,能夠變成永恆的今期流行,已經愈來愈少。媒介變異,群眾分散,口味流動,前兩天大家為IShowSpeed襲港而黑人問號,過幾日到Coldplay登上啟德舞台,街頭巷尾馬上改播〈We Pray〉,歌頌(或鞭撻)Marf 的演出技藝,直至下個熱話來臨。這是香港平民的常態,也是流行文化的本質。
同樣地,試當真結束消息傳出,朋友見我心情欠佳,以「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作安慰;網友羅列其他網絡佳作(如「香城映画」作品),旨在說明一個平台消失不代表時代告終。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這幾天隨意重溫此頻道歷來作品,我除了跟許賢一樣,發現不少短片「真係幾好」(沙石亦不少),還順帶確認,即使如今步向完結,這家土炮工場於2020至2025年走過的路,以至對香港流行文化的意義,其實值得從頭細數。
前世:CapTV工場奠定風格
了解試當真,要先追溯它的前世。
港式流行向來以大台主導,但2014年前後,隨着時代更替,群眾變化,主打創作的小型媒體遍地開花,其中CapTV正是試當真三子相識,以至奠定創作風格的重要起點。當年因工作關係,我曾走訪CapTV大本營,梳理工友們的創作心路,如今翻聽錄音,仍記得這家媒體背後雖是大財團,但員工不足十人,亦無分層結構,是名副其實的家庭式工場。工場資源有限,卻堅持每日一片,生產出來的作品,看來粗製濫造,內容兒戲,當年卻屢屢俘虜人心,全靠兩大法寶。
一是顛覆。CapTV主事人任職大台多年,對說故事的技藝有一定執著,但在堅持言之有物的前提下,他容許年輕創作人於網絡上靈活暴走,自彈自唱。碰撞出來的成品,有些真的不知所云,但亦有不少佳作,言簡意賅,直達人心,同時脫離常規,教觀眾驚歎「估你唔到」。
二是時代。那幾年香港不少人確信,關注社會時事是文明生物的基本責任。CapTV不時以創作介入公共,致力勸說大眾走出豬欄,做好公民,甚至不介意畫出腸道,留下新聞網址,只求觀眾在娛樂和花生以外,攝取更多。事實上,跟CapTV同期誕生另有網台「毛記」,同樣立足本土,以抽乾維港水分為己任,當時不僅撩動人心,掀起狂潮,還由葵涌殺到中環,搖身一變成為上市大生意。一個時代,會孕育相應的媒體,由此可見。
開台:從個人出發 認真與玩笑間跳轉
回顧10年前的CapTV故事,因為2020年開台的試當真,多少承繼了前者的精神,同時不乏變奏。
試當真初期只有四人,一如家庭工場,依賴即時生產,不設存貨。多數短片於游學修家中拍攝,製作土炮,燈光偏黃,特技破爛。第一條短片《寫實的天能》,橋段呼應荷李活巨作,但在嚇死人的主題(及配樂)以外,細心觀眾不難發現裏面不乏「穿崩」場口(連演員擺在路邊的袋都入了鏡),單論技術,這些主打泰式辣醬、假火CG的製作,確如蕭若元當年質疑,屬「家家酒」水平。
但正如當年CapTV,他們真正吸引觀眾的,從來都是故事與創意。試當真最早期短片,既有對舊作的致敬(《魚蛋粉 2》),但更多取材自創作人當下生活,擅長將塵世間最細眉細眼的矛盾(如《唔准搭膊頭》、《IG 朋友》),用戲劇形式放到最大,達至「荒謬中認真,認真中荒謬」的效果(說法來自許賢)。
與此同時,試當真於2019+1年誕生,香港社會環境翻過幾番,昔日CapTV與毛記介入時事的玩法,未必再適用;新時代裏,他們甚少朝向公共,高舉立場,反而多由個人角度出發,聊瑣事,說煩惱(雖則個人事依然反映集體情緒)。即使部分源於輿論、網絡的創作(如《咁大件事冇人講》),內容要不修飾得更為隱晦,要不化身「裝傻的Locker」,留下廣闊的解讀空間(見《再見豬豬》)。
試當真片單之中,最為大眾熟悉的作品,該數2021年許賢和蘇豪主唱的《係咁先啦》,於YouTube至今錄得逾七百萬點擊。香港流行文化的歷史裏,教人聽出耳油的佳作多的是,但能夠像這首一樣,前奏一響,當時當刻的情感、氛圍,隨即撲面而來,恐怕只有極少數。
如此看來,在女、錢、橋、獎以外,Channel其實還需要時代。試當真這種於言志與娛樂(別忘記「試玩毛」系列)之間徘徊、在認真與玩笑間跳轉的取態,令它開台頭一年掀起熱潮,備受注目。觀眾如我,不時為暴走的劇情和諧趣的演繹而捧腹,但收起笑容後,偶爾還會聽見餘韻,眼泛淚光,甚至獲得一種「活着嘅勇氣」(見許賢一周年實體演出的發言)。
經營:燃燒自我 身心俱疲
這幾天,我問過身邊朋友,不少人對試當真初期作品記憶猶新(甚至花數千元成為NFT會員),卻不約而同承認,不知從何時開始,作品看得愈來愈少。這不單是試當真面對的處境——疫情過後,生活復常,圍牆外的人們,要追求快樂,毋須坐困愁城,更不一定以本土優先。於是,2021、2022年過後,不少人由本地流行狂熱分子(逢show必去、逢廣東歌必聽、逢港產片必看),還原為「入場前猶豫、散場後挑剔」的香港典型平民面貌。一如所有流行文化的故事,熱潮會過,觀眾會累,其實是常態。
但單單社會氣氛改變,未足以解釋試當真其後的低落。事實上,經過開台首年的成功,他們不甘於現况,反而躊躇滿志,開闢新版圖:內容上,除了一直在做的劇情片、配音片,還嘗試多搞綜藝節目,真人騷、口試王、研討會,規模愈辦愈大,種類愈來愈多;網絡以外,甚至嘗試做音樂,搞舞台劇,拍電影,衝出葵涌,直達冰島。
要搞新project,自然要更多人手,於是幕後由最初四人,持續擴張至廿幾人,另辦《校花校草》選舉吸納台前新血;人多了,永業街小單位容納不了,Channel需要搬到大 office;花的錢多了,就要多拍廣告,並羅列頻道大計,吸引擁躉課金,鞏固收入來源。
山寨廠癲狂、好玩,但製作工序着重個人,赤手空拳,無法持久。毛記當年嘗試將創作工業化、規章化,僱用車衣女工,大量生產,商業上雖然成功,但質素下滑,嚇走觀眾;試當真初嘗成功後,所走的路又是另一極端:少講規則,不設陣式,創作人繼續不分上下,拋頭腦,灑熱血,燒青春,沒錯持續炮製不少動人作品,但公司上下身心俱疲,瀕臨崩潰,又是必然結果。
如今試當真以「身心健康」為由宣布結束,但其實早於2022年,警號已經響起。翻看偽紀錄片《Channel需要乜》,台前幕後當時已疲於奔命,個別同事因找不着最初加入時的快樂而流淚。那段日子,試當真曾破天荒設一個月「休漁期」,讓創作人與觀眾一同休養生息;此後嘗試建立架構,分工合作,尋找出路。
效果如何?作為外人,自然無法得知;但作為觀眾,我會記得許賢近年兩度在節目鏡頭前暈倒,而三個創辦人在近日直播異口同聲,為結束頻道決定鬆一口氣——因為終於(半年後)有機會停下來,呼吸一下,與家人相聚。
創作往往好玩,經營正好相反;每天化身西西弗斯,把石頭推上山坡的大小工友,如何在燃燒自我、發揚創意的同時,保持心靈強大,身體健康?試當真即將畫上句號,但問號仍然懸在半空。
終結:用行動和創作提出問號
即使步向終結,不代表走過的路、看過的風景沒有意義。
近年我最喜歡的試當真短片,名為《跟住去邊度》,由Ellen和豬文編劇,靈感源自黃子華1992年棟篤笑主題。故事內容講述4個中年人打完邊爐閒聊,你一言我一語,還是無法決定下個目的地,唯有留在原地,相對無言。
翻看留言,不少人鍾情這部短片,是因為它反映時事,點出改用紙飲管的荒謬;我喜歡這個故事,卻因為它並無鮮明信息,反而老實梳理迷惘,收集雜音,呈現死氣,提出問號。今時今日的香港,早已不是10年前感嘆號、破折號盛行的年代;問號有趣,因為它沒有附送答案,反而邀請回應,鼓勵溝通。我相信,它是這個時代裏更為獨特、可貴的標點。
這也是5年來試當真,之於香港的意義。沒錯它不是每條作品都充滿神采,但就如短片最後的白色扭計骰動畫,它至少扭盡六壬,擴闊想像,以行動和創作,為香港流行文化留下過不少問號——香港可不可能拍出《Running Man》般的綜藝show?做幕前藝人,端莊以外,能否開live盡訴心中情?無聊與認真,是否不能共存?壞時代裏除了躺在地上,可否換個姿勢,繼續表達?即使它即將終結,我還是想把這些問號、5年來的回憶,連同豬豬,放在心裏,莫失莫忘。
至於香港流行文化跟住去邊度?繼續問,繼續試,繼續認真,有人,就有下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