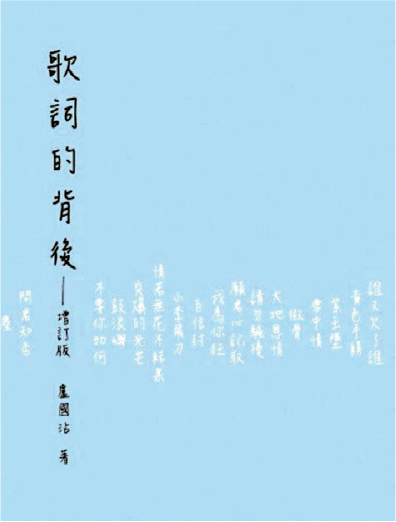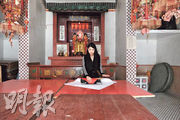【明報專訊】盧國沾仙遊,各界論其功績,例必提及他在1983年發起非情歌運動。余生也晚,當年未懂聽歌,但後來讀到這傳奇般的名詞,實在心馳神往。運動有自上而下者,也有自下而上者,但即使是後一種,像韓柳提倡古文,若非附和者眾也勢難成為運動。偏偏盧大俠這場運動卻由他一人號召,按黃志華《香港詞人系列:盧國沾》的說法,運動在主力兩擊〈螳螂與我〉與〈小鎮〉後,響應者寥寥,「僅一年多一點便無疾而終」。我一直納悶:如此規模也算運動麼?但又有點不服氣,它作為香港文學史上屈指可數有名目的「運動」,倒不應該如此簡單罷。所以姑且不自量力,嘗試勾沉一下這場運動的背景。
欲釐清的幾個問題
就像新文學運動有《文學改良芻議》,盧國沾發起運動時確寫過「宣言式」文章,當然不像胡適寫得那麼理論化,但他顯然是具文學自覺的作者。黃志華編的《盧國沾詞評選》便收錄他在《好時代雜誌》「詞中有誓」專欄其中一篇(書中指見刊日期不詳):
短休復出,我重新檢視流行曲壇的走勢,發覺歌詞的路已改…… 寫歌詞這些年來,我向來不喜歡跟人尾、食人屁。以前我轉寫過「哲理」,結果到「哲理」歌大為流行時,我又轉向「寫實」的,但「寫實」的失敗,我又轉向「愛情與麵包」的。至於寫的方法,我從前寫時,一向題目定得範圍很大,後來把範圍縮小為一個「點」,證實我不停的變,想擺脫自己舊影子。
「復出」後我決定冒險走一條被人勸喻不要進去的路……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冒進這條路子之前,事實上經過一番很費勁的安排。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向唱片公司的人吹噓,獨力製造些輿論……我告訴他們,情歌氾濫啦,滿朝文武都是一個腔一個調,若不出奇制勝,互相殘殺矣。原來唱片公司都有這個感覺,見我一提,就叫我試寫。於是我先寫〈螳螂與我〉……
研究香港流行曲有個難處,就是考證費力。我感到好奇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場運動從〈螳螂與我〉到〈小鎮〉的高峰期,到底歷時多久?關於〈小鎮〉,黃夏柏《漫遊八十年代》引述當時的《年青人周報》,明確指出同名大碟於1983年11月出版。至於〈螳螂與我〉,收錄它的《萊茵河之戀》大碟標明出版於1983年,但哪個月呢?目前維基百科有「歷年中文歌曲龍虎榜冠軍歌曲」條目,相信是有心人整理(偏偏港台官方資料庫欠奉),可惜當年〈螳螂〉並未奪冠。我只好根據唱片編號CST-12-64(CST代表娛樂唱片公司),推斷它出版於同公司《我只有期待》(編號12-63)和《火燒圓明園》(編號12-65)之間,而恰巧兩張碟的標題歌分別在8月及12月登上港台榜首。由此推論,〈螳螂〉約出版於1983年8月至11月,〈小鎮〉接力於11月推出。換言之「非情歌運動」的高峰期,只有短短三四個月。
確立了時間框架,我下一步想追問的是:一、盧先生發起運動時的個人狀態;二、客觀環境;三、他心目中的「非情歌」究竟指什麼。第三項尤易引起歧義,早前盧逝世,坊間不少評論把〈每當變幻時〉、〈大地恩情〉、〈火燒圓明園〉等名曲說成非情歌,若真如此,盧先生何需大張旗鼓發起運動?特別是寫民族情懷的〈火燒〉,明明與〈螳螂〉和〈小鎮〉同期推出,為何不列入運動中?由此可見盧先生發起運動時,刻意排除了以下兩者:一、已成主流的非愛情題材,包括哲理和愛國;二、因劇集而寫的非愛情題材;其實還有第三種,就是1970年代最典型的非情歌,即許冠傑式口語諷刺歌曲(這方面他寫過〈考車牌〉等,但不算成功)。
有關其個人境遇,目前資料是齊備的,因盧先生著有《歌詞的背後》,上面提及黃志華兩本著作也梳理了不少資料。1981年4月,「澳洲幫」入主麗的電視,朝令夕改,盧先生任職該台宣傳部,自感窮於應付,因而減產。1983年初,他毅然離開電視台(已更名亞洲電視),但繼續為亞視寫劇集歌,但隨台勢轉弱,這類作品難復〈天蠶變〉和〈大俠霍元甲〉的熱烈迴響,甚至唱紅這些歌的關正傑和葉振棠等也相繼轉投無綫。本來主題曲是發揮非愛情題材的理想園地,但相信此際他感到此路不通。
他在1982年獲得兩次難得的「包碟」機會,先後為甄妮同名大碟(主打歌〈木頭人〉)及張德蘭《情若無花不結果》填寫全部歌曲,兩張都是廣義上的概念大碟。前者有完整故事,婚姻危機與異國情緣兩線平行發展;後者號稱以顏色為主題,雖有點牽強,但《歌詞的背後》提及部分歌曲說的都是「一觸即發的婚外戀」。他在這兩張唱片試驗了新的寫法,如〈木頭人〉聚焦拆開丈夫來信前的一剎那,就是引文所指的「把範圍縮小成一個『點』」。顯然1982年是非情歌運動的醞釀期,非劇集歌曲將是他實踐新意念的場地。
1980年代初的思潮
那外在環境又如何?黃志華《香港流行曲發展年表》有以下兩條:「1980:樂壇基本上還是電視主題曲的天下」;「1981:唱片業市道普遍不佳」。換言之,踏入1980年代,雄霸數年的劇集主題曲已在走下坡,樂壇也掀起新變化。從1980年至1983年上半年,較矚目的現象有:
一、概念大碟出現:1981年初羅文率先推出《卉》,每首歌專詠一種花,不過題材還是傳統的哲理和愛情。盧並無參與其中,但相信甚受啟發,因為翌年他就包辦了《甄妮》和《情若無花不結果》。
二、民族情懷當道: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前途問題提上日程,1982年更發生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內容事件。就在該年,登上中文歌曲龍虎榜榜首的愛國歌,便有〈蒙塵的巨龍〉、〈我是中國人〉、〈勇敢的中國人〉,和盧自己填的〈大號是中華〉共4首。盧提倡非情歌,偏超越民族藩籬,〈螳螂〉和〈小鎮〉都放眼世界問題,未嘗沒有擴闊大眾視野之意。
三、城市民歌興起:1981年港台舉辦城市民歌創作比賽,並出唱片,1982年永聲唱片接連出版《香港城市組曲》和《靈芝草:香港青年創作專輯》,是熱潮延續。這批歌曲清新可喜,觸及主流較少涉獵的題材,如都市人疏離(〈昨夜的渡輪上〉、〈彌敦道的塵埃〉),還有香港風貌和前途(〈夢到沙田〉、〈一九九七〉)。另外受民族思潮影響,鄉土愛國也是熱門題材(〈望鄉〉、〈靈芝草〉)。盧國沾說滿朝文武都唱情歌,該只針對主流歌星而言。但他或者察覺到,即使寫民歌的年輕人,關注範圍也只集中本土與家國,稍觸及世界局勢只有〈問〉一首而已。
四、新歌手湧現:陳百強、區瑞強、蔡楓華、林志美等先後奪十大中文金曲。而即使偶像派,也不止能駕馭情歌。像《陳百強與你幾分鐘的約會》,Danny作了全碟一半旋律,鄭國江差不多包辦歌詞,寫盡年輕人樂與哀,也具概念唱片雛形,試聽〈失業生〉(原曲是西片《畢業生》主題曲Scarborough Fair):
寒風中街上滿落葉/獨歎息臉上淚還熱/School cert考過等於失業/人生苦短怨恨重重疊……
求職苦爭逐正白熱/運氣差我白費唇舌/僧多粥少此爭彼奪/望休將勝敗論豪傑……
這種寫實題材,在許冠傑時代十居其九用口語唱,且多用於快歌,鄭老師卻證實放諸書面語和慢歌也能成事,而且它的入聲韻也萬分精彩。(說點題外話:粵音入聲的magic實在不容小覷。最近Coldplay啟德演唱會,邱彥筒與Chris Martin合唱We Pray英粵新版,Marf的精湛表現讓對方大為讚歎,竟請她即時do it again。讓Chris為之動容那句是什麼?「學小孩/或學動物/靜靜伴着/萬事萬物」[據說由周耀輝填],這句節奏感之強橫,正是連珠炮發的入聲字和複疊字所致,當然Marf拿揑得極punchy。)
新人可塑性強。唱〈螳螂〉和〈小鎮〉的麥潔文和盧冠廷也是新人,後者更屬創作派,而且有主見,寫中東戰火便是由盧冠廷提議。唱片公司一般較放膽讓新人唱冷門題材,尤其當遇上有想法的新人,自然是詞人交託非情歌的理想目標。
五、新一代詞人崛起:最引人注目首推林振強(不過原來林還比盧年長一歲, 1981年林入行時33歲,盧32歲)。林初試啼聲,〈三人行〉、〈明天怎麼過〉、〈夢之洞〉等無論題材筆法均不同凡響,這是否觸發了盧同行較勁的心態?實情不得而知,但當盧把反戰的〈小鎮〉寫給盧冠廷時,林在同一唱片也交出了講世界大同的〈青色小怪人〉(靈感來自ET)。高手心有靈犀,暗中互相砥礪,也不是沒有可能。
由此可見,1980年代初樂壇非情歌思潮湧動已久,不過如此具創作自覺,能正式發起運動者,盧先生是第一人。
逆主流而行的兩擊
那盧先生心目中「非情歌」該是何模樣?還須回到詞作本身。
〈螳螂與我〉寫螳螂隨難民流亡,一方面用螳臂擋車之意,喻平民勢弱難敵戰火:「萬里饑荒/不足養一隻螳螂」;另一方面藉昆蟲生存本能,象徵難民之意志力:「只有螳螂/不響半聲向後望」。詞末寫螳螂跳船失去蹤影,戛然作結,尤突顯寓言性質。全詞以蟲比人,好戰者視人命如草芥便不言而喻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詞中難民投奔怒海之場面:「一隻孤舟/正奔向暮色東方」、「風裏黑海哪裏是岸/痛苦絕望聚滿小艙」,他一早就寫過了──對,就是1980年膾炙人口的〈大地恩情〉:「若有輕舟強渡/有朝必定再返」。
據盧自言,他童年時被迫渡船離開故鄉潮連,辭別生母:「江邊送別的,是我媽媽。畢竟年紀太小,還不知是離鄉別井,所以連一句道別的話也沒講過。這是我從不原諒自己的事情」,〈大地恩情〉「骨子裏是寫我二十多年裏的怨嘆」。適逢越戰結束,大量越南難民湧港;而中越交惡,越南驅逐華僑,也有大量人民逃到中國。盧先生因緣際會,接觸到一些華僑,他坦言曾把這題材多次偷運到歌詞裏,包括1980年〈何處見段落〉和〈異鄉人獨白〉,因為「越南華僑事件是華僑史裏最為慘烈的一次」,不過這些歌「在無聲中面世,因為我悄悄地寫,沒有打算告訴任何人」。可以說,寫〈螳螂與我〉他已蓄勢數年。
至於〈小鎮〉,他稱這反戰題材在香港「似乎以前從未有人這樣做」,大抵是誇張了,至少鄭國江早於1980年為羅文填過〈號角〉。關於寫法,他自言刻意運用視角變換,分別是「鷹望向地面、垂死人望鷹、視平線見婦人懷抱孩兒」,並把自己扯出鏡頭,純用客觀呈現。此詞動物意象也具多重寓意:「鷹低飛看見了十數人群/啊…恍似蚯蚓」,無疑是策動戰爭者之喻,但隨着鷹的嘩叫聲與炮火聲交織一片,有若狂歡:「哎喲喲…鷹歡呼似愛上炮火聲音/啊…鷹飛小鎮」,便彷彿暗示人類宿命,就像漢樂府《戰城南》和魯迅《藥》的烏鴉,大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反諷象徵意味。
縱觀兩詞筆法,雖不像英美同類歌曲運用長篇敘述(如同期Billy Joel和Bruce Springsteen分別寫越戰的Goodnight Saigon和Born In The USA),但顯然講故事成分增加了,流露以詞寫史的野心。他延續前作「專寫一點」的試驗,以動物視角映襯人間戰亂,一首以昆蟲仰觀人潮,另一首以猛禽俯瞰飢民。可以留意的是,講故事需要較長的歌詞篇幅,而這兩首旋律,正好都開始擺脫1970年代短小的AABA曲式:馮偉棠作曲的〈螳螂與我〉是罕有的AABBB結構,盧冠廷的〈小鎮〉雖屬簡潔AB結構,卻重唱了兩遍。要不是曲式延長了,相信盧國沾也難以施展敘事魔法。
非情歌運動確是了不起的嘗試。概括盧先生的意圖,大抵有:一、運用文學筆法;二、刻意寫非主流題材,甚至帶自覺的作者意識,不止把歌詞當成代歌星言的商品。要是這場發生於1983年下半年的運動成功了,會否把香港樂壇引到另一方向?
這當然是假設性問題。1984年初,盧國沾仍為麥潔文填了〈龍壁懷古〉和〈唐吉訶德〉,算是運動的第三、四擊。同期他也為譚詠麟和甄妮填了〈傲骨〉和〈夢想號黃包車〉,但因為是紅歌星,只好退回較為人接受的勵志路線。與此同時,樂壇迅速倒向偶像化局面,break dance舞曲成為炙手可熱的曲種,單是林振強一年內就填了〈愛到發燒〉、〈創世紀〉、〈震盪〉,還有麥潔文轉型之作〈電光霹靂舞士〉。盧國沾呢,這類官能刺激似非他所長,他為夏韶聲填的〈不顧一切警告〉也說明拒絕跟風的心志。他此後最重要兩首力作,是繼續深化詠史筆法的亞視主題曲〈武則天〉和〈秦始皇〉。
至於林振強,看似走上一帆風順的商品化道路,不過他暗地裏一直從事非情歌實驗,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