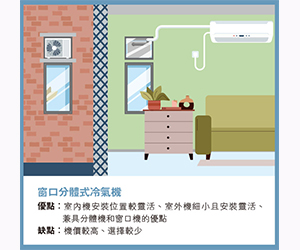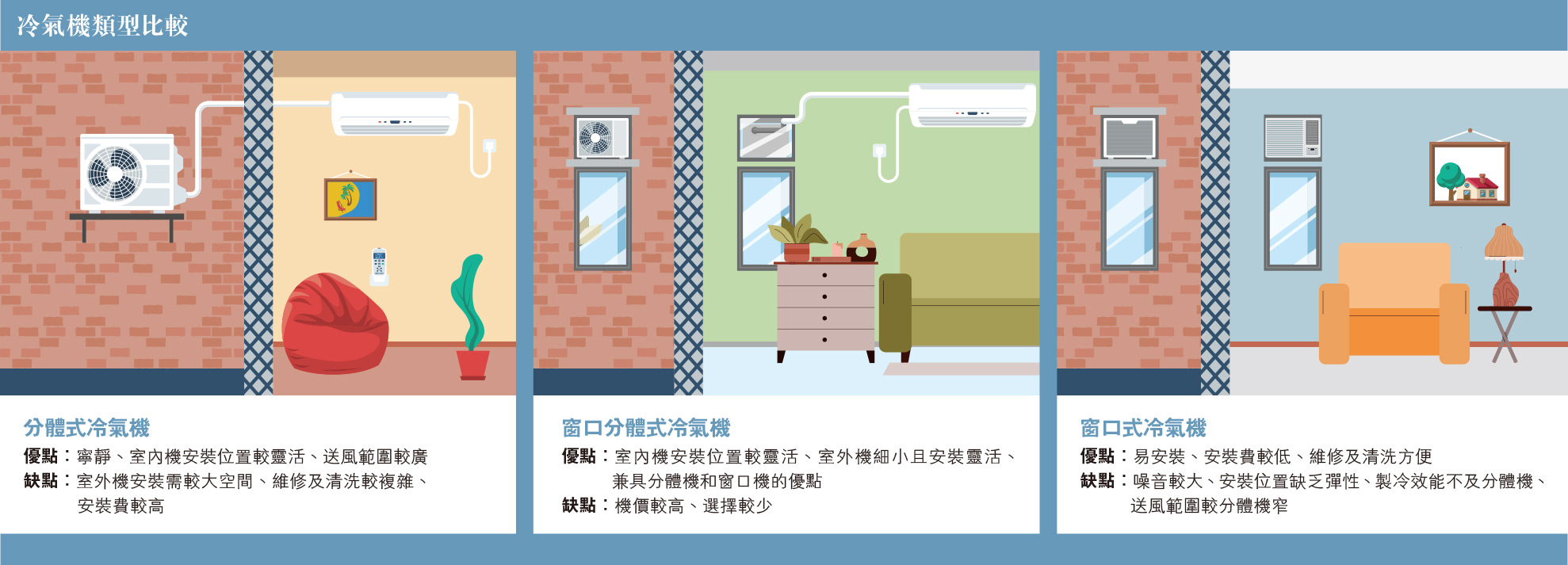【明報專訊】金馬獎將於周末11月27日揭曉。10月初,獎項的提名名單公布,入圍的香港電影包括一部叫《少年》的,角逐「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輯」兩項。當時,大部分人沒聽過此片。《少年》是任俠、林森兩位年青導演所拍,以2019年「反送中」運動為背景的劇情長片。他們以極低的成本、非常機動的方法,默默完成。故事是關於救人的。2019年不少年青人受抗爭運動所牽動,意志消沉。有人想自尋短見,網絡有群組自發,透過蛛絲馬迹搜救。影片主角是少女YY,7月28日星期天早上,她在網上發放出絕望的信息。然後一整天,好幾個與她素未謀面的年青人,穿梭九龍新界,爭分奪秒、千方百計要找出她的下落;同一時間,各區的抗爭仍在熾熱的爆發。幾星期前某天於九龍城,我們談起這齣大部分香港人無法看見的香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