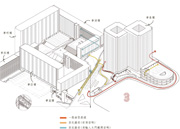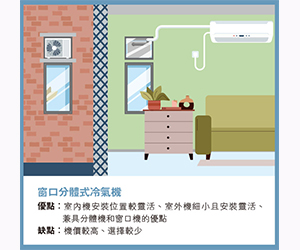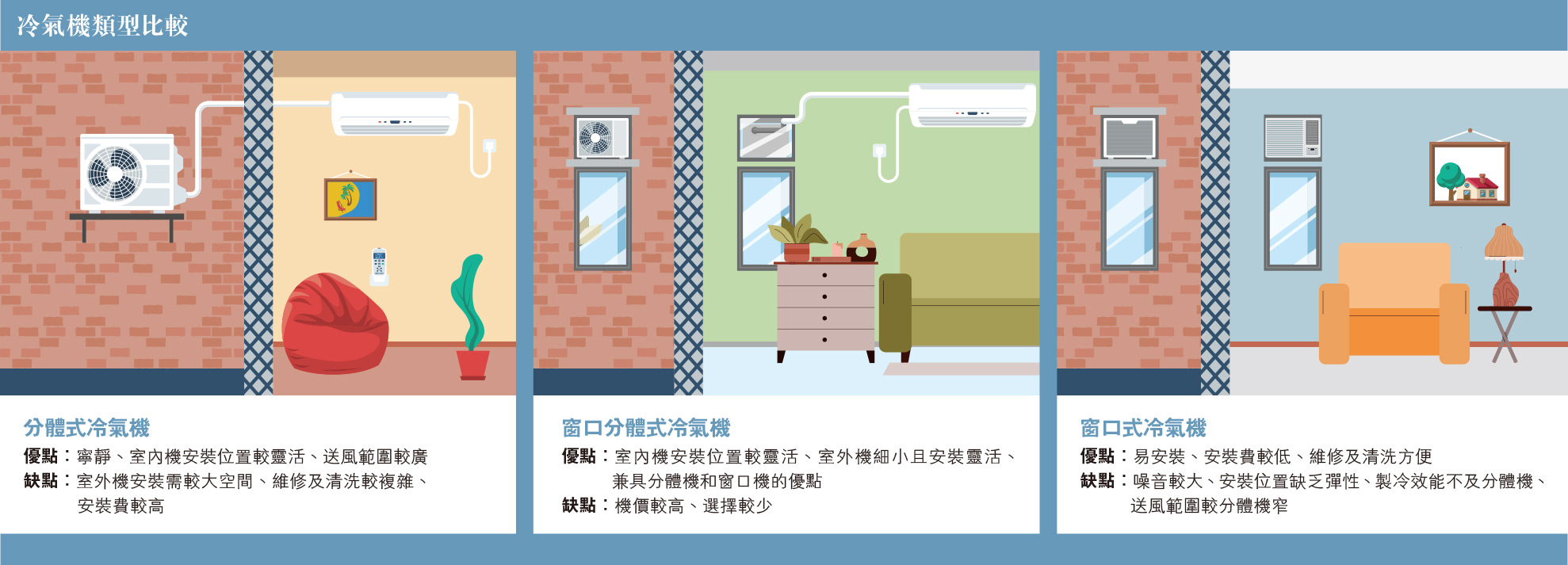【明報專訊】疫情記者會每天匯報有多少高齡患者死亡、多少安老院舍爆疫,「長者不敢外出,日日在家看電視、數數字、嘆氣,『今日去世的92歲,我90歲,不知幾時輪到我』,便有些負面想法」。這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榮譽顧問區結成身邊的真實例子。雙老難堪其中一人久卧病牀,不惜違法助其「解脫」的慘劇亦有所聞。不論香港或外國,長者政策尤其是醫療方面的流弊,在疫情下顯露無遺。「全球的醫療思維自從鑽進COVID後就跳不出來。疫情其實影響我們如何看待生命晚期,但因為不是生死數字的問題,沒有人認真和全面地看。」疫症奪去不少長者性命,也驅使他們思考死亡、計劃終老。
長者疫歿數字低 不等於成績好
先談疫情與長者的關係。區結成說,社會較關心因探訪規限而與親人相隔的感人案例,但較少留意防疫抗疫措施,怎樣削弱上門支援服務和社區資源。「抗疫成績表」只看有多少長者入院和染疫去世,忽略長者生命晚期的身心需要,「純粹用數字看生命,減少長者死亡數字,特別是院舍長者,似變成醫療最終目的。但對很多長者而言,生命延長少少未必有意義」。他以往經常到院舍作外展服務,見到不少高齡院友因病而活動受限,不能自理甚至要穿約束物,就算未有疫情,每年死亡率亦約為10%至20%。「醫療目的是否讓長者在照顧不足、不能探訪的情况下,困在院舍延續生命?讓他們今年不死於疫情,然後遲一年死於其他病痛,就等於好成績的想法,是否有點不合邏輯?」相反,他認為應在長者晚期照顧投放更多心思,令他們享受最後一段時光。
另一方面,疫情對長者的身心影響逐漸浮面,如美國正探討獨居長者因疫情而面對社交疏離和缺乏醫療援助的問題;同時開始提倡配套完善的老齡社區。在香港,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月前分析顯示,長者在第五波高峰時的自殺個案倍升。中心總監葉兆輝稱在首四波未見有明顯升幅,相信長者的焦慮或壓力累積至第五波才爆煲,如眼見封區、家人檢疫或隔離、院舍撤離等,「隔離或檢疫雖是7日、14日,但他們未必有清晰時間觀念。家人突然沒來探望、沒有家庭聚會,對他們來說都是好長時間,以為被忘記、遺棄。我們需要特別關顧獨居或有病的長者」。支援和資訊不足或觸發恐懼,釀成慘劇,有確診獨居長者怕傳染家人及有後遺症,於家中隔離時自殺。葉兆輝說疫情是最後一根稻草,「不是疫症本身,是以前的安全環境打亂了。政府應該檢視長者服務和疫情安排引起的混亂」。區結成補充,防疫方向會影響社會對疾病的看法和整體氣氛,「是把疾病想像成四方八面籠罩的恐懼?或是接受人有患病風險,保護自己、注意健康就好,這會間接幫到長者重拾信心」。
感院舍長者受困無助 醫生:社會應討論安樂死
區結成另一擔憂,是在安樂死或協助自殺合法的地區,或有更多人在疫情下以此了結生命。外國引入安樂死後,人數通常會穩步增加,但加拿大在2016年引入協助自殺(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MAiD),他說有研究顯示申請數字在疫情期間急增,孤獨感是主因之一,相信長期社交疏離、抑鬱和無望的社會氛圍,會令人產生負面生命看法,「普遍都有抗疫疲勞,被疫情拖低對生活的情緒、興致」。
養和醫院前副院長鄺國熙倡議安樂死多年,年近90歲的他初步計劃赴瑞士安樂死。有感疫情下院舍長者受困無助,認為刻下社會有再次討論安樂死的必要。行醫多年,他眼見晚期病人苦况,也只能加大嗎啡劑量,減輕其痛苦;現時雖有預設醫療指示(AD)、紓緩治療等選擇,但他認為尚不能解決問題。他以自身為例,因大手術後有失眠、情緒困擾等問題,需長期服用多種藥物,令他精神萎頓,生活質素大降,不能如往昔般自由活動,自覺失去尊嚴,「生命是神聖和有尊嚴的,但人都應該有自由和自主」。
普羅市民難負擔
他慶幸有能力到外國安樂死,且得到家人支持和允諾陪同,但強調並非所有病人都能抵受舟車勞頓,普羅市民更難承擔出國支出,故仍主張香港應設安樂死。他長年整理檔案和剪報,見到多宗雙老家庭誤殺案,均是老伴見另一半病榻纏綿,希望助其解脫,有的更明言希望安樂死合法化。他相信由醫生把關,可避免濫用情况,正如他到瑞士,也需向當地醫生證明自己的病况難以忍受且不可逆轉。但對於曾要求安樂死的鄧紹斌(斌仔),鄺國熙在2004年則表示反對,因當時斌仔的情况正在好轉。另外,反對安樂死一方也憂慮滑坡效應,如政府會因此節省其他治療開支,或將安樂死由絕症或晚期病人放寬至其他非末期病人上,如加拿大近日有人因長新冠申請MAiD。區結成觀察,比利時和荷蘭的安樂死均較寬鬆甚至有濫用情况;美國俄勒岡州則一直嚴格遵行自1997年實施的《尊嚴死亡法案》。
香港生死學協會創會會長伍桂麟則從病人角度想,「安樂死」三字看似一了百了,或會減低病人積極尋求治療方案的意欲。除非長者能掌握充足資訊,才有條件推行安樂死,伍說:「香港於20年內會出現好多中產獨居,特別是子女移民的長者,他們希望預早規劃人生,不易受傳統約束,自主性比較高,或可有這選擇。」
其他選擇:試行院舍離世 推動健康老齡化
除了思考安樂死,疫情亦令更多人認識到AD、預設照顧計劃和在家離世等選項(見4月24日本欄文章「晚期照顧篇」)。善寧會營運總監及賽馬會善寧之家院長陳木光說很多人因疫情驟然離世,驅使長者思考怎樣早作準備,部分亦主動交代身後事,「若等有事發生,家屬才去了解,但已去到臨時臨急,沒心機再聽,很多時已太遲」。業界見到長者在醫院孤獨離世,亦想引進其他切合長者需要的做法,如已在歐洲推行的院舍離世。有些長居院舍的長者已視院舍為家,多數希望在熟悉環境度過最後日子,但因香港法例要送到醫院,現有疫情更無法見到其他院友和院舍職員。
可結合社區醫療資源
陳木光說香港若要試行院舍離世,可先為職員提供臨終護理培訓,同時結合社區醫療資源,由醫生恆常到訪,提供身體檢查;院舍職員代為到醫管局藥房取藥,免卻長者折騰。「香港院舍的營運是住宿為主,外國則是提供終老地方,讓他們開開心心,像個大家庭,好重視健康生活。」
長遠而言,陳木光期望香港推動健康老齡化,讓退休人士保持活力健康,像歐美會為他們物色不同的義工崗位,文員、教師各適其適,務求讓長者接觸外界和資訊,保持智力和正面情緒。「這樣可減少好多無謂的晚期痛苦。較積極的長者會定時做身體檢查,及早診斷和治療疾病。」他見過不少抱病長者在伴侶離世後不久就過身,「情緒很影響人的健康,如果能從容面對壓力,到將來自己面對晚期時,都會較正面」。
其他國家的長者照顧在疫情下也有所改變。例如西班牙是區結成認為在生命晚期醫療方面做得較好的國家。因疫情嚴重時護老院和日間護理中心爆疫,當地很多長者轉為選擇家居護理,政府也因此增加相關撥備,坊間開始探討派護理員住在長者家中的可能。另外,澳洲長者院舍的晚期服務一直較全面。在疫情期間,墨爾本有的安老院和退休村仍能維持適量聯誼活動,院友在村內步行運動,早點、下午茶、消夜依舊不缺。多間機構仍然能提供面對面的長者護理服務,更會為受疫情影響的長者提供免費援助。
了解長者真正所需
縱然上面探討了多個方向,但其實長者未必能清晰表達自己心意。安寧服務社工梁梓敦粗略計算,疫情期間有約10%長者個案曾跟他提及「想死」、「想快點死」,並不會說出「安樂死」或「紓緩治療」之類的明確字眼,「我們要先理解背後的原因,如果解決到,他未必再有這個想法」。他相信這些長者未有選擇尋死,是因為尚有身心需要,才會尋求社工或身邊人協助。他會按情况提議在香港可行的選項,如跟醫生討論換藥、提供紓緩治療、跟家人溝通等,「每個人的最後決定都在自己手上,如(溝通後知道)他其實是希望安樂死,只能告訴他香港現時沒有此選項」。資深護士林詠芝曾協助過一名有死亡焦慮的伯伯,雖然他選擇在家離世,子女輪班看顧,但他仍一直不敢入眠,因為害怕一合眼子女就會離開。於是林詠芝建議子女晚上握着伯伯的手睡覺,讓他知道家人陪伴在側,最終伯伯在睡夢中安詳辭世。如命途多舛、已去世的燒傷康復者黎少鴻所言:「死亡係對等,但死之前嘅痛苦唔係平等。」疫情下數字大過天,我們會否忘記了,如何讓長者走好最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