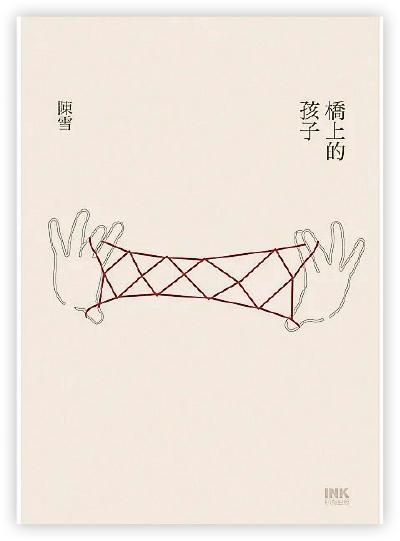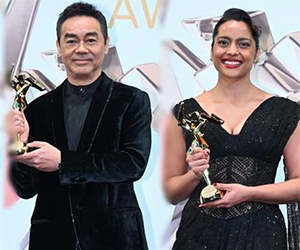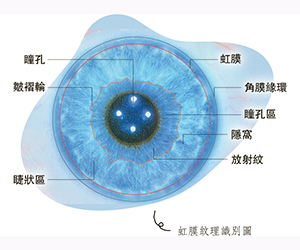【明報專訊】二○○四年,陳雪出版小說《橋上的孩子》,宣傳文案稱其為「作家首部自傳體長篇小說」,把書中有關主角隨父母於夜市擺攤叫賣、母親可疑而無法判別時長的離家、父母投資失利欠債遭人白眼,以及主角為堅持寫作而不得不自家庭與情人身邊逃開的書寫,與作家本人身世扣連。十八年後,她出版散文集《少女的祈禱》,把這些童年記憶整理成一本書,並說:「這本書,我認為是要過了五十歲才能寫的,我不知會否過早,但這剛好是個想寫的狀態。」
書寫的原動力:匱乏與追尋
《少女的祈禱》(下稱《少))源自陳雪於二○二○年時曾連載的散文專欄,原先只有六期,但寫下去發現,自己好像不曾以較舒淡的方式處理童年,似乎大多包含於小說裏,遂有了把過去經歷發展成書的念頭。於是全書篇幅從原有以聚焦個人童年、青春期至大學畢業後的生活境况,慢慢撒展成網,擴寫至作家本人周邊形形色色的人物,把其成長置身的一九八○年代,勾勒拓撲。如〈紅樓夢與十二軍刀〉描繪離家到城市上班的母親及其煙視媚行的姊妹們的飛揚神態,在夜市裏幫忙高聲叫賣;在城市的公寓內夜夜笙歌,然每天醒來,即盛裝打扮,轉身便是外出應酬的艷麗佳人;〈流浪者之歌〉則如《清明上河圖》般仔細敘述流浪夜市的攤位動線與人流推移,乃至每一店家的細描,最後匯成群像,讓作品多添一份江湖味,也成了時代的紀錄。
初讀本書,或會疑惑其文體應歸為小說抑或散文,乃因結構相當特別,書中首篇〈迴旋曲〉為「序曲」,以一種既帶夢幻感又不確鑿的腔調回憶主角童年時去酒店探望母親,卻迷失於所有門牌、裝潢、地氈皆一致的旅館設計中;另外在四輯分隔間,又插入了三篇〈夢途上〉,連出版時都特地以灰紙裝幀,以資辨識。會有這樣的結構,與陳雪的小說家身分有關:「可能因為我是小說家,我認為結構會帶來意義。透過不同結構,可把這些回憶組成不一樣的東西。我寫的時候很樸素,但希望透過特別的組織,讓作品看起來更複雜。」
陳雪又談及〈迴旋曲〉的結尾:「後來成年的我,於是做着一種工作,叫做寫小說,但事實上,我只是重複那個下午旅館走道長廊上的發生,就是那將耳朵貼在門板,企圖動用經驗、想像、幻覺、記憶,將隱藏在看似一模一樣,永無止盡的白色房門內,其中一個母親的房間尋找出來。如果沒有,那麼,我就自己創造出一間來。」
她認為,這也是其文學觀寫照——那些不存在的、想要的、尋覓的東西,透過創造,把它生出來。「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一個核心力量:匱乏、追尋,尋找媽媽,尋找正確的記憶,或是已流逝的時光,它們都會成為創作力量。寫作可以撫慰你,可把失去的、已消失的東西找回來。」
從小說到散文:如今,這是我的故事
若是陳雪的忠實讀者,在《少》中必定能發現不少其過去作品寫及的場景、題材、事件等——這些小說碎片,皆可在書中找到對應(印證)。當中契合點最多的,或許是作家於二○○四年出版的《橋上的孩子》(下稱《橋》)。比對兩本作品,《橋》是「自傳式小說」;《少》則是「帶小說感的散文」,要重述經驗,何以在多年後,選擇置換文類?
「我自二○○一年起寫《橋》,當時以小說切入,是希望有所區隔保護。我覺得小說是虛構的,它讓我把不能寫、難以啟齒的東西,透過小說形式作轉換,成為一種隱喻。」那時陳雪三十出頭,剛開始意識需處理家族與童年創傷的反噬。然陰影如猛獸,不可直擊,必得從旁探視,更憂心讀者會把文本與作者扣連,於是選擇以小說書寫:「其實『自傳式小說』是一個很弔詭的詞,小說是虛構的,但自傳又是……這不是很奇怪嗎?其實我當時就是不想別人認為,這是我的故事,我才寫成小說。年輕的我不會寫散文。」
從《橋》到《少》,感覺從「孩子」走到「少女」,再走到「女子」。相較《橋》沉重撕扯如陷入死胡同的書寫,《少》則有種傷口仍在,卻有和煦陽光暖暖曬過的節制溫柔感,是因為經年後,心境有所轉變,還是文體置換使然?
對陳雪而言,兩本書的經驗述說雖有重疊之處,然作品的母題與時間性卻截然不同,因而影響文類選擇。她解釋,《橋》處理的是(當時的)當下和負罪感,三十出頭的主角,放下原有家庭位置,不顧一切逃離家鄉,以獨白式喃喃自語,是告訴讀者,也在重組自身:「我」是誰?為什麼「我」現在這麼奇怪?如今的「我」是怎樣生成的?那些被重述的過去,皆為指向當下、即時的「我」的存在。
「然而《少》不一樣。《橋》說的是成年後的敘事者,如何被過去影響;《少》則是事過境遷後,已沒那麼糾結和內疚,家裏的問題也已解決了。因此我終於能相對客觀冷靜地,看待那些曾讓我很痛苦的事。我覺得心態不一樣。」昔日難以啟齒的創傷,在經歷時間翻攪,洗滌,稀釋後,終於不再推開,反是納入懷內,承認這是自身故事,是屬於她的記憶:「三十歲的我沒辦法寫一本回憶之書,當時的記憶並不完全,而且,當時還是太近了,仍很受家庭影響。很多事情都是如今的我才能較具體去看,《少》我認為是要過了五十歲才能寫的,我不知會否過早,但這剛好是個想寫的狀態。」
記憶的再現與真實性
房慧真為本書撰序時,曾指「小說家復刻場景的能力令人驚歎,像照相機般的瞬間記憶能力。……她在其中採集素材,除了以擅長的說故事能力驅動,將萬花筒下繽紛的舊世界細筆描繪、拓撲出來,亦見功力。」在《少》的多篇散文中,可見陳雪對景物描述的細緻度如鏡頭追貼,需仔細確切得如像素清晰,從空間場景、人情物態等,皆必須以極其「真實」的姿態照見;然而在逼近後,書中不時「誠實」地自我反詰對重塑回憶的質疑——那段極其清晰的描述,是真的嗎?抑或是虛構的?要再現記憶的真實與虛構,陳雪指,這一直是她在書寫裏處理的事。
「到底記憶是什麼?記憶是被呈現出來還是被提取出來的?它可像檔案般被提取後直接讀取嗎?我曾以為是這樣,後來發現,不對。記憶會隨你的不同狀態而改變。」她認為,每次想透過書寫去再現記憶時,弔詭的是,每次重寫,都會讓記憶的輪廓有所轉變,或因心情、年紀、對事情的印象等而被影響,致使及後的再寫,都難以判別其時腦內篤定的回憶,到底是確切發生過的,還是某次書寫的印象。她以夢與作品為例,五十多歲的當下,作家已寫過二十多本書,做過幾千個夢,有時會混淆有些事情到底是她曾經歷過,抑或是寫過的小說,還是做過的夢?多年來在作品一直辯證「記憶的可信與虛構」,如今陳雪有了舒懷的答案。
「有可能我們的人生正需要這些不同版本的提取和再現,再把它們全部拼湊在一起,或許這樣才會形成一個全景。這全景可能仍是殘缺的,但它是層層疊出來的效果,有些破碎,有些疏漏,有些空白。我們的人生也如是,它未必如你想像打開,拼完了,就能完整。起碼我覺得我的人生全景不會是一個真正的真實,而是透過堆疊而成的。」細想下,或許人的記憶本就存在斷層,很多碎片化的畫面,或是非線性的,關鍵在於如何,及以怎樣的材質填補縫隙,小說家則選擇了敏感細膩的筆觸。
經驗重述與必要的書寫
回歸作品本身,《少》雖是作者的回憶書寫,讀來卻顯輕盈,尤見於對人物從外到內的勾勒,像是輕描淡寫,抓住神韻與靈光,就淺淺幾筆描摹而成,點到即止。如〈遙遠的琴聲〉寫「我」小時候去學鋼琴備受音樂老師疼愛,至及後另一個光鮮女孩小如加入後,三人間微妙的小心理;〈黑暗中的星光〉也寫「我」上補習班時與另一個優秀男生疏離而含蓄的惺惺相識。這些描摹中,不僅是對他者的凝視,而是相當自覺地,在凝視中回歸自身的省思。陳雪笑說,這種筆調與其成長,乃至其後的創作觀相關。
「我小時候因為家裏的事,受到很多欺負,也經歷很多荒謬的處境,讓我覺得做人絕不能這樣,不要馬上判斷他人。這也形成我後來寫作的特色,我跟很多人來往,都會觀察他們,先放在心裏,盡量不多做判斷。」因此《少》的人物們,都不是旨在定性為好或壞人的二元對立,反是更細膩形塑每個個體的立體面,她續道:「在處理這些回憶時,我都盡量淡化,不強烈去描述,淡淡地寫,讓看的人自行判斷。在這本書裏,我想盡量保持自己幼時的態度。人在長大後,經歷多了,會根據習慣或價值觀去批判,但這本書我刻意略去這種色彩。我希望回到小時候的視角,哪怕很痛苦,仍要當一個公平的人。我想保留這種狀態。」
書的尾聲,作家如此自白:「我生命裏的故事總是被我一再訴說,可是又無法說得完整。」綜觀陳雪多本作品,可發現好些情節、人物、事件時在反覆出現,皆指向同一原有經驗創傷來源。「反覆搬演及書寫經驗」這回事,是「不得不如此」的書寫嗎?在多次意圖以訴說靠近回憶,卻時有「遺失」、「扭曲」,那是一種治癒還是持續的傷害?
「我剛開始寫作時,其實完全不寫自己,因為小說可以虛構。我是為了不想成自己才寫作的。」陳雪苦笑:「我是到了三十歲時,那時去美國,發現自己好像到了必須處理這些事情的年齡,而我只能透過書寫自身來挽救自己。我那時寫完《橋》和《陳春天》,也有種焦慮,怕人家說我重複。然而那時我覺得,別人的說法不重要,我必須要寫這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經年後,陳雪在書寫自身以外,也已寫出眾多優秀的小說作品,但再述自身經驗的欲望,卻一直未減,對她來說,這是必要的寫作。「我覺得人的記憶和經驗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被重敘的,關鍵在於每次的重寫,對其時的作者本人有什麼意義。這個意義未必在寫前就發現,這就是書寫的原因,我們必須通過寫作,才能反過來洞察自身,為什麼會寫出這個,為什麼這樣寫。」關於重述經驗的意義,她這樣總結:「沒有什麼經驗不能寫,或被限制只能寫幾次。當然有些書評或讀者會有其看法,覺得重複,但有時候我們書寫不是為了某些人。更多時候,我們需要以自身作品來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