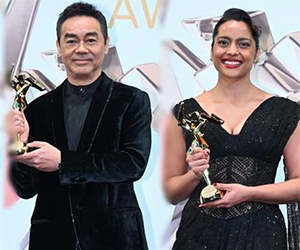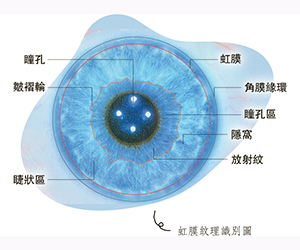【明報專訊】幻想眼前有道精緻的秋日菜式:蘆筍薯蓉配白松露片,你會是那刨得剔透的松露?挺立翠綠的筍尖?或可會是被削走的薯皮、一把切掉的蘆筍莖?近日,有支持本地食材的餐廳搬演「它的神話—植物宴」,將3道菜結合虛構神話和形體表演。食物設計者說,與其長篇累牘地闡述剩食和生產系統問題,不如用一頓飯打開觀眾的感官,由此細思形塑眼前食物乃至自身的社會制度及價值觀。
「不二菁」與「萬千同」
一開始,表演團體TS Crew徐緩步出,俯伏在餐廳正門,然後像草木萌發般騰身躍起,於地上鋪灑樹皮,引領觀眾就座。室內佈置似叢林祭壇,桌上點着蠟燭,掛有肉薑和南瓜等農作物。如枝蔓的表演者在走道伸展軀體,虔敬地接過廚房的第一道菜「不二菁」。中空的蘋果醋漬白蘿蔔,夾着脆嫩的櫻桃蘿蔔片和璇蔓豆苗,旁邊有如花瓣的球莖茴香片,幾乎不用費力咀嚼。負責食物設計的團隊「深食」成員陳可兒說,食材意味餐桌的精英制,食客追捧米芝蓮三星,要吃萬中無一的食材,同時反映大眾的價值觀。而的確,大家面前的明明是同一道菜,但觀眾想拍照打卡時,仍會不期然比較,選出擺盤最標致的一碟。
隨後,表演者在鋪滿樹皮的地板匍匐,任團員踏過他們的背和雙腳,像在攀過嶙峋石壑,再將第二道菜放在角落的長桌,如同供奉神明的祭台,又似現代自助餐吧台的擺法,提示觀眾動身自取。菜名是「萬千同」,用倒模一樣的豆腐凍呼應追求統一的審美標準,奇形怪狀不容於主流,這不一定在高檔餐廳才見到,「有時因為價錢考量,去光顧快餐和連鎖店,人們都預期一式一樣的食物。很多對食物的預期和期待都有成本,最後由環境承受。或(套用在社會),是由光譜以外的人默默承受」。
「河」與「無極」
氣氛漸轉,表演者替對方穿上祭祀的新衣,從橫樑取下布卷,沿走道延展。有成員在場邊用節奏口技和混音器配上迷離的音效。其他人舉起名為「河」的紫椰菜水,往杯裏滴檸檬汁,液體在觀眾眼前變成藍綠色,預告第三道菜「無極」,會將前兩道的基調扭轉。它是街頭小食炸油糍的變奏,把其他菜式去掉的「蕪雜」變作餡料,包括蘿蔔皮、椰菜和茴香葉等,寓意混沌世界。至此,那個「它」終於揭盅,神話的主角「神獸」是無極,代表現實世界的真象,而第一和第二道菜均是它的分身。「表面是珍惜食物的議題,希望從一些吹毛求疵、變成犧牲品的食材,拓展到考試制度的優勝劣敗。希望食物設計交代到這樣的層次。」以神話貫穿,是深食近年常探索的手法,因陳可兒認為所謂神話傳說,都是因應當時社會運作而生的「說法」,「科學論文以外,這些敘事都建構我們的價值觀」。
以形體代替文字、旁白
活動的策展人呂幗昕邀TS Crew用形體說故事,想拉近食物與身體的聯想。團員曾將加入當代元素的舞獅帶到愛丁堡藝穗節,也到過橫濱TPAM表演藝術會的前倉庫場地和法國蓬聖埃斯普里的古蹟演出,但在餐廳是頭一次,還要身兼「侍應」。由帶觀眾入座到示意大家進食,TS Crew始終不發一言。觀眾近得可以看見團員額上的汗水,他們在做「疊羅漢」等難度動作時,大家都揑把冷汗。該團藝術總監曹德寶說,在港未見過有同類跨界合作,外國只知有蔬菜管樂團。是次以食物設計為表演藍本,不同團體以前結合古今藝術的方向,他最初的想像較為直接,「與食物有關係、我們見過的,好像都是很直接的行為,例如關於浪費食物,就在你面前將食物糟蹋,用此行為刺激觀眾思考」。事前雖有食物設計圖,但原來對他來說太抽象,他憑着神話構思和一堆形容詞,才想出由輕到重呈現整頓飯。「我們傳菜、拿碟的手勢,有個狀態,很集中地做一件事,這牽涉到動作質感(movement quality)。」他以喝水的動作為例,可藉時間和空間處理來傳遞信息,「可以很慢地喝,全神貫注地看着那杯水。你只是見到動作,已聯想到很小心。這是舞蹈和編排要放進去的」,亦正是觀賞當代舞的原理。所以整頓飯不用文字和旁白,觀眾也能明白。另一伏線,是他們開首鋪墊的樹皮,觀眾會感到腳下凹凸不平,「表演者跟觀眾的連結,由邀請他們走進去那刻開始」。其後表演者躺臥甚至層層疊時,觀眾或能一同想像,感受到痛楚。
當植物成為神話主角
食材都是蔬果,陳可兒說對食物設計有限制,但更符合題目中的「它」,「想像一隻牛有價值和生命,比想像一棵菜心容易。今次將植物擬人,創作成神話主角」。他們有意念和主旨、備好設計圖,還得靠餐廳Rooot的廚藝和經驗。深食設計第二道菜時是夏天,本想用冬瓜配上漬物,但至11月已過當造期,故改成豆腐,有同樣神聖的外觀和清甜味道。另外又參考壽司擺盤,加上竹葉,引出豆腐的清鮮和方便進食。傳統炸油糍要用長柄模具逐個塑形慢炸,難以同一時間備好數十份,廚房想到先焗後炸的做法,蘸上甜酸醬汁,使油糍中的「菜頭菜尾」在口腔內「歸於一統」。
Rooot負責人郭鷹傑曾專程到上海觀看沉浸式劇場Sleep No More,對演員引導和打破觀眾期望、開放觀眾感受的手法尤為深刻,憧憬着把這類體驗帶到餐廳,例如讓食客先觀看農夫由插秧到收成的紀錄片,之後才品嘗食物。籌備這次活動,他帶着批判:「三餸飯、兩餸飯,你又在吃什麼?可能是『冰鮮千年肉』?價錢真的主導所有?」廚房團隊來自五湖四海,米芝蓮餐廳和大牌檔出身都有,故能應付到風格迥異的三道菜。食材多出自Rooot的林村農圃和本地農夫,他最喜歡那沁甜的茴香片,說分量本應不止這麼少,因雨水和蟲害令收成大減,他要從附近農場東拼西湊,「不是太多人種,也不易種。因是根部植物,底部最甜,蟲經常在泥中咬,不下農藥的話收成都很少」。有的食材卻要減少分量,如豆腐凍上有塊炸番薯片,沾了話梅粉。本身其實是炸番薯條,但試吃時人人吃不停,他決定換掉,「不想只為『醫飽個肚』。是否要吃到很飽?打着嗝抱怨說很飽?」
觀眾挑食帶來思考
雖然打着反思剩食的名號,現場所見,還是有人吃剩紅蘿蔔片或挑走食用花。「很想走過去(向觀眾)說:你試試這個,好好味的,這個得來不易。都有這種心情。」但轉念一想,這個始終是劇場體驗,一桌人都有不同食法,「至少感受過,我們為這頓飯絞盡腦汁,他們欣賞背後有這些默默耕耘的農夫或本地種植」。深食視食物為創作媒介,從不設下規條或用說教的方式,成員伍澤均舉例說,即使某人將食用花擺一邊,或也令同桌人思量,「如何證明它可不可以吃和它的存在價值?食用花在這其實是重要的調味料,觀眾覺得是裝飾的話,反而會錯過了一些東西」。
他們在餐桌「埋下」不少思考位:有人研究棕櫚葉碟是否可吃;看着如高級餐廳的菜式,大家你眼望我眼,不敢下箸;油糍底有塊春卷皮,未必個個懂得將它包起。伍澤均明言,這次體驗只佔參加者一日三餐中的其中一餐,重點不是要將人們不吃的統統從菜單拿走,或是呼籲大家吃清光,「食物是起點,終點是食物以外」。這頓飯或不能讓觀眾飽腹而去,但會滿腦思緒。
何謂「食物設計」?
食物設計由西班牙設計師Martí Guixé在1997年提出,涵蓋所有與食物相關的設計,包括食器、加工、包裝和空間等。陳可兒和拍檔伍澤均於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畢業,她說香港食物設計多關注食物本身,例如醜食(ugly food)和食物系統韌性(food system resilience)。「我們不是看作食物資源的問題,更多是社會想法,例如為何要崇尚精英和追求標準化的世界。」伍澤均舉快餐店為例,「為什麼這樣盛行?如果人們不是只有30分鐘午飯時間,或者口袋不是只有30元,會不會想食快餐?」他們認為食物「易入口」,較易與各類背景的公眾交流,故一直用食物創作,例如在香港動植物公園設計多款小食,包括呼應英殖時期的維多利亞蛋糕,讓遊人了解古蹟及古樹的歷史,以及思索香港身分;又曾為小學生設計港式包點,包括「原條魚柳包」和「腸包仔」等,由他們決定「吃或不吃」和定義藝術品,也讓成人反思加諸下一代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