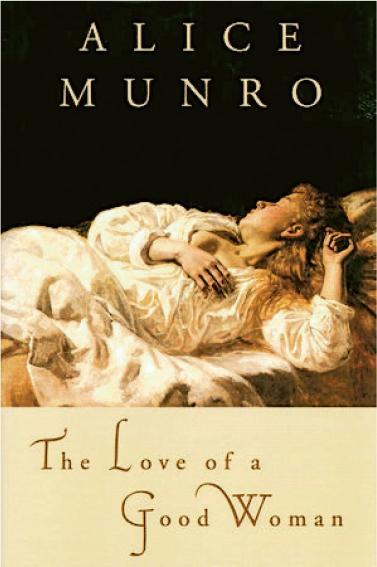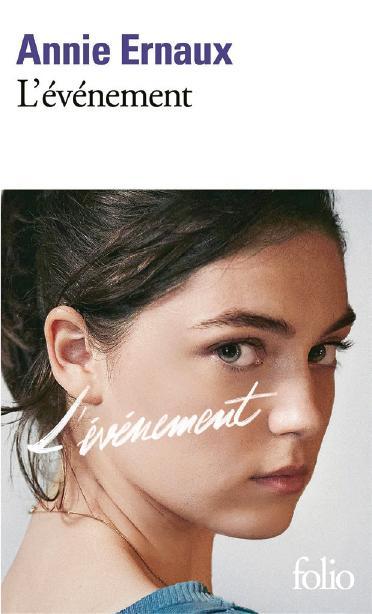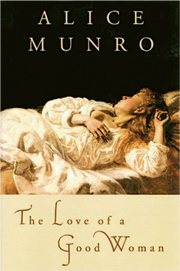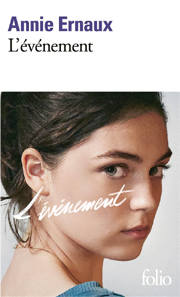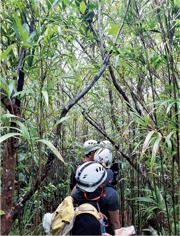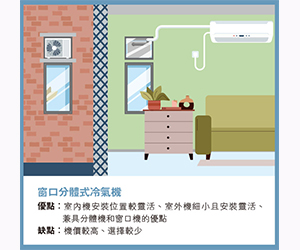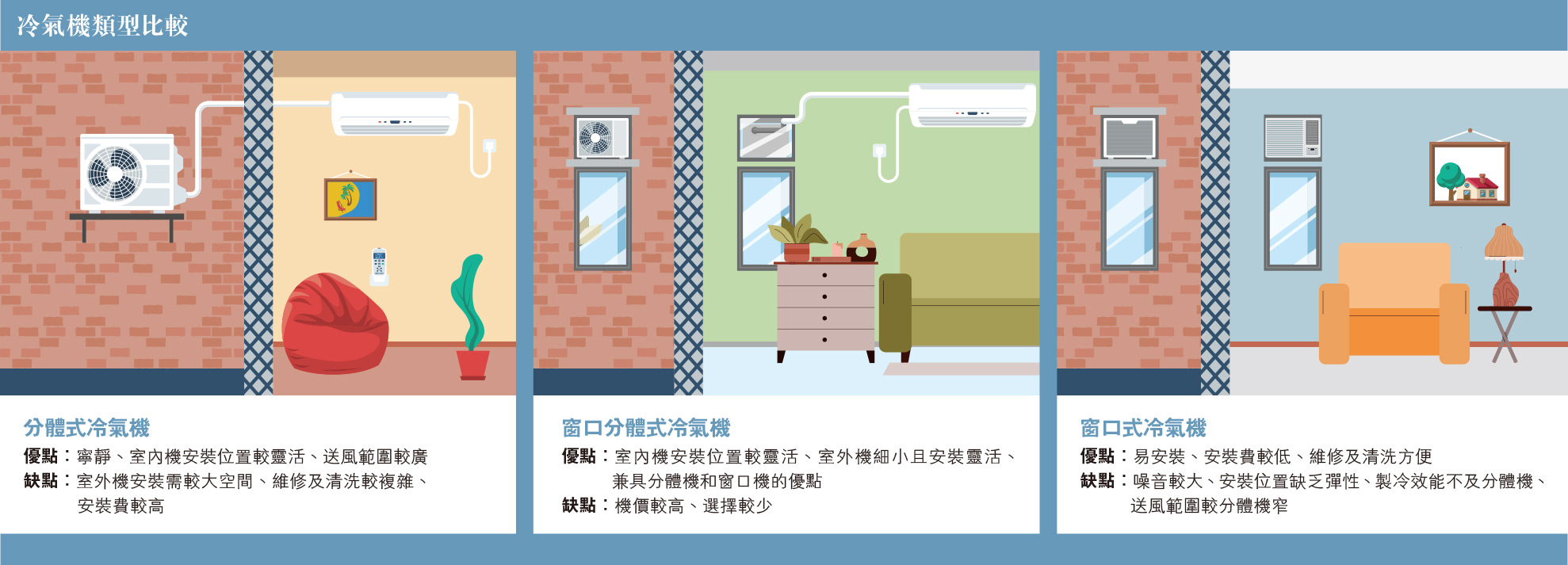【明報專訊】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20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則在2022年獲獎。如果上網搜查對這兩位作家的形容,「女性作家」、「女性主義」等字眼一定會出現。她們是如何看待女性作家的身分的呢?孟若自己是擁抱女性作家這個身分的,她曾說過:「我的故事當然是關於女性的,因為我是一個女性。我不知道這個詞(按:女性主義)對那些寫男性故事的男作家來說是什麼,我亦總是不肯定『女性主義者』的意思是什麼。一開始時我曾經說過,好吧,我當然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如果這意味着我追隨某一種女性主義理論,或是對女性主義有一定理解,那麼我並不是。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因為我認為女性的經歷是重要的,而這些女性的經歷是女性主義的基礎。」孟若說自己沒有追隨某種特定的女性主義理論,她只是寫女性的經歷,而這些經歷,她認為是女性主義的基礎。同樣,艾諾本人在法國參與了幾十年推動女性權益的社會運動,是法國女性主義其中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不過她在一次訪問中也說,她其實不過是一個寫作的女性而已(I'm just a woman who writes - that's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