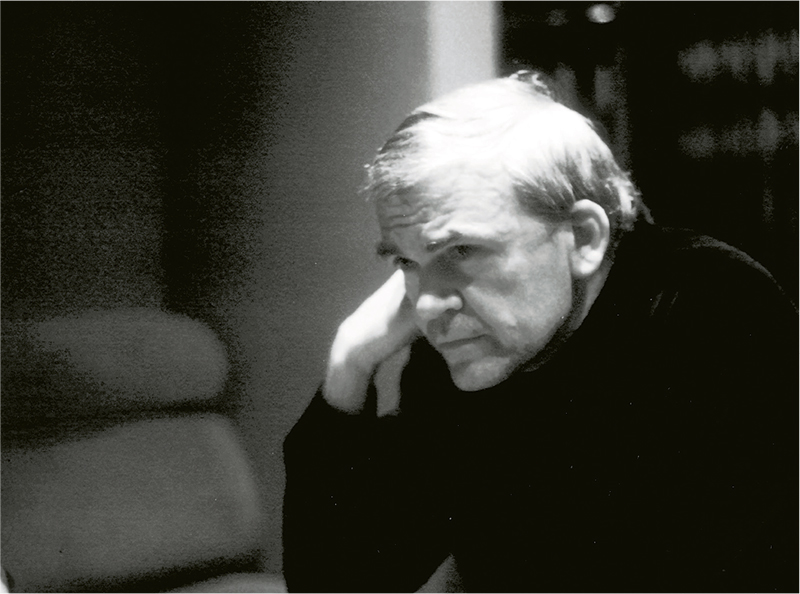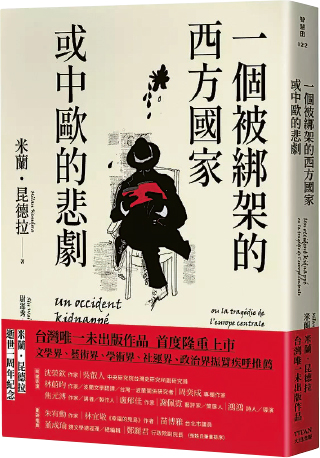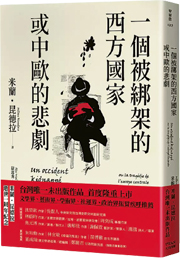【明報專訊】米蘭昆德拉在某篇文章的開首中,提到一段歷史:1956年,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國內的革命運動,一名匈牙利通訊社社長在其辦公室被蘇軍炮火摧毁前幾分鐘,向全世界發放了蘇聯入侵匈牙利的消息,並以這樣一句說話作結:「我們將為匈牙利也為歐洲而死。」昆德拉的問題是,為什麼將當時匈牙利的命運等同於歐洲的命運?在這篇名為〈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的著名文章裏,他試圖給出一個解答:對一個生活在共產主義鐵幕下的匈牙利人來說,捍衛匈牙利就是捍衛備受威脅的歐洲價值,這名匈牙利人才會向整個歐洲發出這樣的呼喚;然而昆德拉卻悲觀地認為,歷史的現實卻恰恰相反,匈牙利慘遭蘇聯蹂躪,正說明了「歐洲」不再被視作一個整體價值和身分,在鐵幕之外的歐洲,即昆德拉筆下的「西方」(Occident),並沒有聽懂這位匈牙利人的呼喚。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1983年,當時昆德拉已離開捷克,在法國定居。一年之後,他出版其巔峰之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自此,昆德拉儼然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捷克文學代表,而這種「西方凝視」的眼光,則對昆德拉的自我身分認同產生了影響。這篇文章中的一個關鍵表述「一個被綁架的西方」(Un Occident kidnappé),在原法文版本以及根據法文譯出的中文譯本中,都沒有直接解釋這一表述含意的段落,但在英譯本卻有一處提及:
「這是一個西方的悲劇—— 一個被綁架、流離失所和被洗腦,但仍堅持捍衛自身身分的西方。」 (it is a drama of the West—a West that, kidnapped, displaced, and brainwashed, nevertheless insists on defending its identity)(中譯為我按英文版本譯出)
在原法文版本及中譯本中的同一位置上,則是以下一句:
「而恰恰是中歐的悲劇。」(mais précisément comme celui (le drame) de l'Europe centrale.)
這段文字本來要說的,是關於幾個昆德拉提到的中歐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都曾經發生過反抗共產主義政權的起義,並且得到廣大人民支持,但結果卻全都是失敗收場,而這一件事,並不能視為東歐、蘇聯或共產主義的悲劇。於是,法/中版本和英譯本中,我們讀到這個「悲劇」分別被解讀為「中歐」和「西方」的悲劇。昆德拉當年發表這篇文章,被法國知識分子界視為昆德拉對西方的指控,文首提及的雖然是一個匈牙利人的故事,但昆德拉卻理解為一個「中歐」的故事,因為他當時正「無可救藥地覺得自己是中歐人」。
「中歐」的矛盾形態
這種身分認同,構成整篇文章的立論基礎:位處我們一般理解的「東歐」與「西歐」之間,有一個複雜並充滿矛盾和不確定的地區,昆德拉稱為「中歐」。他認為中歐文化屬於西歐,但政治上則位處共產主義東歐,這個矛盾形態造就了中歐的命運,其精神文化和身分認同全都建基於它的處境:歷史上,中歐民族是歐洲多樣性的縮影,但同時又長期活在兩大強大帝國的陰影下,即德國和俄國。在昆德拉所身處的冷戰時期,歐洲被分為東西兩部分,這種對立與劃分可追溯至古羅馬分裂,但昆德拉卻斷言,或說是在他的歐洲意識影響,他將東西歐視作同源於古希臘和猶太——基督教傳統,而中歐,則是歐洲文明內部分裂中的緩衝區、多樣化表現甚至是璀璨瑰麗的文化遺產,正如文中他反覆援引幾位他所景仰的中歐文豪,如卡夫卡、布洛赫(Hermann Broch)、穆齊爾(Robert Musil)和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後來昆德拉在別處稱四人為「中歐文學四傑」。他們超越了民族與國家,以其「中歐人」身分照光了偉大的近代歐洲文明。
恰恰是在這種認知之下,昆德拉將中歐被蘇聯強行劃入共產主義東歐這一件事,看成是一場「西方」(西歐)的悲劇,這是因為這個「西方」被騎劫了,人們以為只有西歐才能代表歐洲,因而將中歐當作東歐的一部分排除於外。這才是真正悲劇之所在。
這篇文章在昆德拉去世前不久才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書中還附上另一篇早被遺忘的文章:〈文學與小國〉。這是昆德拉在1967年的一篇演說講稿,當時他仍在捷克斯洛伐克,內容意識上跟1983年那篇文章的最大差異,是他當時並未有清晰的「中歐意識」,而只知道「民族國家」跟「歐洲」之間的對立。他批評當時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一直抱持着一種狹隘的本土主義,並未意識到捷克作為一個「歐洲小國」的價值。昆德拉的建議是:要以小國精神,努力讓自身的文化上升至歐洲乃至世界的水平,而不是盲目自大地捍衛虛妄的民族自信。
昆德拉亦如此歸結捷克人在歐洲認同上的兩個選項:「要麼讓捷克語弱化到最終淪為單純的歐洲方言——而捷克文化淪為單純的民俗——要麼成為一個具備一切條件的歐洲國家。/只有第二種選擇才能保證真實的存在。」
要注意的是,在演講之後一年,就發生了「布拉格之春」——就是昆德拉後來所講「西方或中歐的悲劇」的一個重要情節。那時捷克正在鐵幕邊緣,昆德拉在講稿中沒能明言的是,捷克民族主義的狹隘本土主義其實是依附強大帝國(蘇聯)的條件,於是他的呼籲就變成了要求捷克「脫俄入歐」,前提是要讓捷克文化(昆德拉主要關注文學)達到歐洲(西方/西歐)水平。從這一脈絡看,他後來所論述的「中歐」,根本就是對他出國流亡前這篇講稿的理論的深化,當中亦符合昆德拉本人的思想變化:他從一個民族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歐洲主義者,在法國定居以後,他的對話對象則由國內同胞變成西方社會,而他的論述場域,亦從自身國家民族變成整個歐洲。他作為一個被辨認為捷克人的小說家,卻長期在捷克國內遭到冷待,「中歐」就成了他調解箇中矛盾的身分位置。
這兩篇文章於冷戰結束後30多年才結集出版,在當下這個歐洲乃至世界的語境裏,我們重讀當年昆德拉的思想轉折,又可以讀到什麼呢?
歷史當然會永遠記住柏林圍牆倒下和蘇共倒台這兩件結束冷戰的事件,但對於昆德拉念茲在茲的歐洲和中歐而言,尚有一件政治事件應當被提及。2004年,有10個國家同時加入歐盟,是歐盟版圖擴張最為激烈的一次,而當中正包括了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這四個昆德拉口中的「中歐國家」。昆德拉曾在文中說過,這些小國的命運跟英法德俄等大國之不同,是「小國族」(petite nation,昆德拉用語)總是處於想像自身可能會消失滅亡的憂患意識裏。中歐小國熬過了冷戰,脫胎成獨立自主的國家,然後在2004年加入歐盟這個號稱在政治上將歐洲一體化的組織。乍然一看,昆德拉的論述好像已不合時宜了。
「共同體」的異質性
當然我們還可以談得再仔細一點。在歐盟於20世紀下半葉的漫長形成過程裏,歐洲思想界也曾深入討論過「歐洲共同體」這一論題,比較著名的有南希(Jean-Luc Nancy)、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思想家論述過的「共同體」,他們試圖指出,「共同體」的陳述並不意味着絕對的一體化,反而是充滿着複雜的異質性;而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則在其著名有關「疆界」的論述裏,強調疆界作為共同體的邊界,同樣並非清晰明確,而是曖昧混雜處處。這些討論,間接回應了昆德拉所講的「中歐」。之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上述的共同體討論乃是架設在後冷戰的政治背景上,它首先假設,共產鐵幕倒下,歐洲人終於可以專注實現構想超過一世紀的「歐洲一體化」了;然而思想家們卻又一再告誡我們,剛性的共同體既不符合歐洲的現實,也不符合歐洲的理想模樣;同時間,政治現實又再一次翻轉人們的主觀意願:今天的俄羅斯繼承了共產主義東歐的遺產,只不過東西歐的邊界在歐盟的構作下向東遷移了,兩年前俄烏戰爭爆發,人們也清楚看到,那條邊界現在位於烏克蘭,而不再是昆德拉的「中歐」。
那麼,「中歐」還存在嗎?存在的,但卻是在歷史傳統裏,而不是在共時的歐洲共同體框架中。不只是《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這部著作,在昆德拉很多文學評論裏,讀者所讀到大量的偉大文學家名字,幾乎無一是20世紀下半葉的人。他褒揚拉伯雷、塞萬提斯,近代的則頂多近至卡夫卡,那都是他所要追認的歐洲文學精英。但這種文化價值,儼如是精神貴族式的宣言,它彷彿在說:歐洲有着一個偉大的文化文明傳統,而中歐民族則因其災難式的夾縫命運,而具備繼承並創新這一偉大歐洲文明傳統的條件。先姑且假設他的論斷正確,但在21世紀的當下,中歐不再是昔日的中歐,歐洲小國也沒有昔日的悲痛命運。當我們再談論捷克文化,或中歐文學時,昆德拉40年前的想法是否然已經失效?
非民族的精英文化傳統
又或者,我們引用另一個關於「中歐」的說法。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1996年寫過一本題為《大幻影?一篇論歐洲的文章》(A Grand Illusion?: An Essay on Europe)的小書,裏面提到:「中歐」完全是一個近代概念。朱特認為,所謂「中歐」,很可能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這個統治了中歐地帶達數百年的王朝,創造了像布拉格、華沙、布達佩斯或維也納等赫赫有名的城市,它們的城市文化構成了所謂的「中歐文化」,而非由各個民族所決定。而且,這些民族長期弱勢,一直無法建立自身國家,而需依附在傳統大國旁;民族之間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都很大,要辨認他們的身分,主要是以否定詞的方式來進行,如「非俄國人」、「非日耳曼人」等。朱特更指出,他們的精英必須在大城市中流行的普遍理念(如「歐洲」),跟狹隘的地方主義中抉擇,這恰恰就是昆德拉在〈文學與小國〉中的說法。
朱特的分析,緊密地將昆德拉作為中歐知識分子的身分意識勾勒出來:昆德拉追認的「中歐」,是一種非民族(不是「超民族」)的精英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自有其城市性質,但在昆德拉筆法,卻僅僅是說「不可能是政治性的邊界,而是共同的大處境」。我們大概可以如此設想:例如用「德語作家」或「捷克作家」來描述卡夫卡,都好像不及說他是「布拉格作家」來得合適;布洛赫以及很多20世紀初的天才德語知識分子一樣,都是維也納文化圈的一員。可是,即使在昆德拉的時代,在民族國家浪潮高漲跟冷戰鐵幕徐徐落下的年代裏,這種「小國族」的共同大處境似乎已非昆德拉所描述的20世紀初那個模樣,正如朱特所批評,標榜「中歐傳統」,最多只是一種懷舊。更何况當中歐已成西歐,東西歐邊界已遷往烏克蘭這個正面對當代「大處境」的國度時,昆德拉的說法或許仍然適用於某些位處大統一國度邊緣的地方,例如烏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