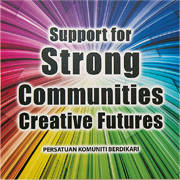【明報專訊】無國籍人士不被任何國家承認為公民,從教育、醫療、工作到居所等,幾乎無法律保障。現代人生活有多便利,他們的生活相比之下就有多匱乏。羅興亞難民是最大無國籍族群,被稱為「最不受歡迎」和「最受迫害」的人。在檳城的羅興亞人,不受馬來西亞歡迎,但他們不認為身處孤立處境便要絕望地等;十數人成立難民網絡,為出生在海外,從未踏足過緬甸家園的新生代同胞,開班授課,社群間互助自救,離散下亦不用虛度光陰。
背景
項目:馬來西亞檳城羅興亞難民在無國籍狀態下互助自救
目的:讓在他們在被重新安置到已簽署《難民公約》的國家前,有受教育的機會及得到基本權益
人物:Penang Refugee Network組織幹事與活動參加者
大馬政府不承認難民身分
無國界醫生估計,截至今年8月,全球羅興亞人口有約282萬,其中超過75%正在海外生活;依人口數量排序,孟加拉的最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馬來西亞其次。到本世紀末,預計會有70萬羅興亞人誕生,每5個新生兒中,只會有1個曾到過緬甸家園,所謂民族的根。
記者在馬來西亞採訪期間,到檳城南部區域,訪問Penang Refugee Network(下稱PRN)組織幹事Abu、Mumtaaz和Angeline,談出路和希望;他們要求在報道中隱去姓氏,以避免警察查詢或民眾騷擾。
PRN辦公室位於一個發展失敗的花園式住宅區中,跟遊客認識的檳城美食天堂、打卡、度假聖地等印象大相徑庭。樓上舖地址不好找,團隊在沒開滿照明燈的辦公室中隱身。正當我以為,這個團體的氣氛可能如馬來西亞羅興亞難民的處境一樣灰暗,推開半掩的鐵門走上樓梯後,卻見到他們的海報,標語寫着「Support for Strong Communities Creative Futures(支持發展強韌、有創意的社群未來)」。
的確,馬來西亞羅興亞難民的處境孤立。儘管馬來西亞的主流宗教與羅興亞人的信仰同為伊斯蘭教,但馬來西亞未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缺乏協助難民的制度與資源。逃到馬來西亞的羅興亞人,法律上是「非法入境者」,沒有歸化為公民的途徑;若無聯合國難民署簽發的難民卡,隨時可被捕。因憧憬「穆斯林兄弟情」而逃到馬來西亞檳城的無國界醫生社區義工Muhibullah,便說在當地的生活是「肉隨砧板上(my status is in someone's hands)」。
想讀書?不能讀主流學校。想工作?沒有工作許可……在獲聯合國難民署安排,重新安置到已簽署《難民公約》的國家前,他們所欠缺的基本權益,可以不斷延伸。可是,這是否代表檳城羅興亞難民只能乾巴巴地等?Abu、Mumtaaz和Angeline不認同。
受助者長大後回饋同胞
Penang Refugee Network連結難民的方式,是在多個羅興亞人社群聚居地開班授課,辦講座和一起做運動。他們有兩支男子足球隊,女生也會定期打羽毛球。跟香港的中小學生一樣,羅興亞小朋友會上英文、科學和電腦課。這樣簡單的生活,卻是PRN突破多重難關,承受警察頻繁查詢的壓力下爭取得來的。
PRN在2018年由獨立社區協會(Persatuan Komuniti Berdikari,下稱PKB)協助下成立。馬來西亞人、同為PKB組織幹事的Angeline說,他們在2012年開始支援難民。「有一日,一個難民找到我們,說他自己在客廳辦了一間幼稚園,問我們能不能幫忙。」Angeline解釋,那間幼稚園未經註冊,無法籌款,經營困難。「我們就想着要註冊成立一間NGO(現在的PKB),可以幫他們籌錢,申請資助。」
PKB隨後聚集了一群有心的羅興亞難民,是PRN的雛形。Abu說,PRN是同胞自發成立,「他們有不同困難,想找人幫手聯絡NGO,或尋求建議,同胞就會召集願意和有能力幫忙的人去協助。一段時間後,曾經接受過幫助的人主動提出,我願意幫忙,我想成為一份子」——不如成立一個團體的想法,從而誕生。
Abu今年21歲,在2011年從緬甸逃到馬來西亞,一直住在檳城。逃亡前,他正讀小學;到檳城後經同胞介紹,到有心人自組辦學的小學上課。完成小學後,他沒有機會升學,於是隨父親到建築地盤工作,偶爾到學校當助教。「其餘時間我只留在家,因為什麼都不能做。」Abu說。之後,他接觸到PKB等團體提供的兼讀語言課程,開始學英文後,他能夠幫同胞寫字、填表和與人溝通,「有時幫人填出生證明書,有時幫手申請津貼和(聯合國難民署)難民卡」。
他7年前接下語言課程恩師的教職,成為英文課老師,「他看到我的潛力,問我有沒有興趣教書。眼見同胞的教育程度落後於人,我覺得教書是我對社群的責任,得到恩惠後,要回饋其他人」。
恩師現時已經重新安置到已簽署《難民公約》的國家,而Abu就在公餘時間進修「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已經在吉隆坡考完4個科目中的兩個;證書相當於美國或加拿大高中文憑,對於日後工作、升學有幫助。他也義務擔任社區個案工作員,跟進同胞因非法居留被拘捕,也教他們熟悉難民可使用的醫療服務(如無國界醫生的診所),以及使用叫車服務程式Grab等。工作雖微小,他們希望同胞不會感到孤立無援。
冒查封風險 免費辦學
身處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按無國界醫生的估計,約有21萬人,其中約一半獲聯合國難民署簽發難民卡,由於申請者眾多,當中不少人仍在等候申請獲批。PRN服務的羅興亞難民中,不少人是無卡者,服務他們有被警察查封的風險。正在經營一間學校的Mumtaaz對此感受頗深,「警察經常來檢查,問我們有沒有登記、誰資助我們、我在哪裏住……」
Mumtaaz說很害怕,「我有75個學生,他們很多來自孟加拉(Cox's Bazar)難民營,(因當地情况惡化二次逃難到馬來西亞)沒有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卡。如果警察查到他們的話,我什麼都不能做,他們會被拘捕。對,就算是小孩也會被拘捕」。對於不計成本,酌情不收學費辦學的她來說,被警察頻繁詢問,更多的情緒是憤怒:「我好驚訝,我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校可以讀,我才辦學,你還要這樣質問我?」
不過,Mumtaaz身為羅興亞難民的一員,見到現在社群和PRN的進展,感到欣慰。她在18歲時與丈夫一起來到馬來西亞,喜歡讀理科,但苦無求學途徑,便在網上自學,後來進修僅有的民間課程。她現在的學生,小至4歲,大至16歲,已經有較規範的課程可讀。「從孟加拉和泰國過來的羅興亞難民,有的已經14歲,仍不懂寫『ABC』,我會教她們,也教女生少有機會學的生物和化學科。」
育有兩個女兒的她,談起女性同胞的弱勢和遭遇特別痛心。她擔任社區個案工作員,手上有約50個案,也會在課餘時間推廣性相關知識,尤其是避孕措施和童婚的壞處。Abu補充,童婚在羅興亞難民中是難題,他見過最小12歲的女孩結婚,她說:「(在原居地的)安全問題和父母的財政壓力可能促成童婚,加上看到年少女兒在家什麼都不能做,可能會覺得結婚更好。」但Mumtaaz說,童婚經常伴隨未成年懷孕,對身體絕對是壞事,他們要透過教育,避免這類事情繼續發生。
盼妥善安置:難民可貢獻社會
「嗡嗡嗡嗡嗡……」訪問期間,記者聽到檳城定期噴灑滅蚊劑的機器聲;這對於Abu和Mumtaaz來說已是日常,未等我開口問,他們就已解釋。已經在這裏住超過10年的他們,熟悉此城生活資訊,只是未曾被政府和社會接納為國民。
Angeline認為成立PRN,已經是檳城羅興亞難民「Creative Futures」的一部分。她大學時到海外留學讀法律,見到其他國家的多元族群組成很有趣,「你可以從不同人身上學到許多」。回國後,她發現馬來西亞的異鄉人難民,是社會中最脆弱一群,「基本上什麼都沒有」,被民眾歧視,「如果政府有妥當的途徑安置難民,他們可以貢獻社會,事實上他們已經在貢獻社會。拒絕承認他們的存在,只會令事情變糟」。
政策沒改善,不代表羅興亞難民要望天打卦。Angeline已經服務了難民17年,但說PRN現在數百人的規模,要歸功於難民自己的創意和毅力——誰能預先想到他們會透過WhatsApp群組,連結分散居住的社群?他們不是被動、等待幫助的人,現在甚至能自行寫計劃書,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申請資助。
當然,受限於大馬法律,PRN無法為羅興亞難民處境逆轉乾坤,如遇上無卡者被捕,他們無法到拘留中心探望;但合眾人之力,他們可以為被拘捕者的家屬提供食物援助,也能向難民署等機構報告,為他們倡議,「把事情推進多一點(spring things up)」。
接下來考取「普通教育發展證書」後,喜歡讀歷史的Abu未必能如願在馬來西亞讀大學,因為儲蓄有限,「可能要把機會讓給跟我同一年級的弟弟」,但至少得到求學和應試經驗,他可向其他好學的同胞分享。長期被視為無望的羅興亞難民,有朝一日或會是馬來西亞大學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