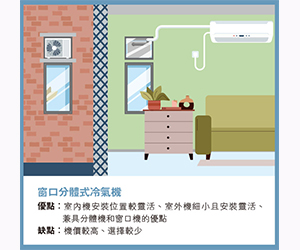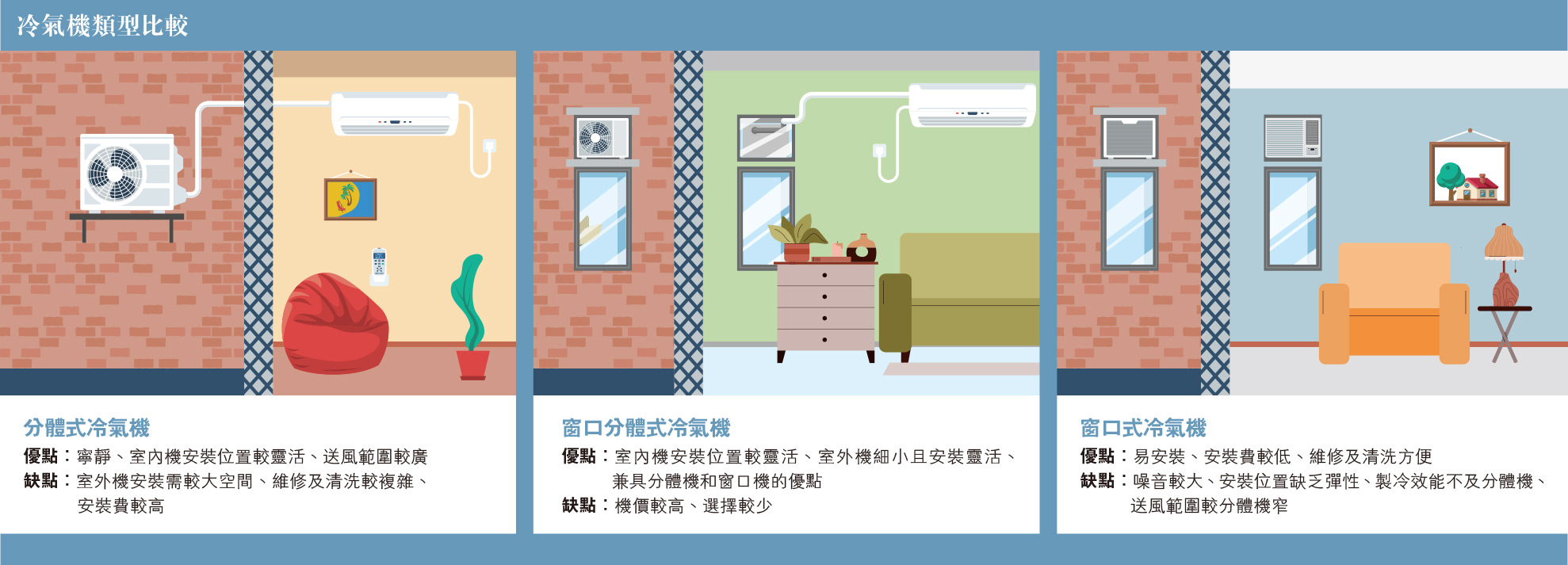【明報專訊】要談創傷,以色列導演Shaylee Atary是過來人,8年前車禍導致她不便於行,執導的短片電影Single Light則改編自遭性侵的經歷。肉體的傷與心靈的痛無法比擬,去年10月武裝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Atary與當時僅一個月大的女兒倖存,惟其丈夫、同為導演的Yahav Winner為保護二人慘死槍下。Atary近日帶同Single Light訪港,片中主角遭性侵後壓抑情感,嘗試如常過活,相伴在旁的友人好比黑暗中一盞救命燈,安靜而強大。現實中,她藉電影創作治癒傷痛,以音畫探索創傷過後的生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