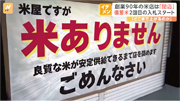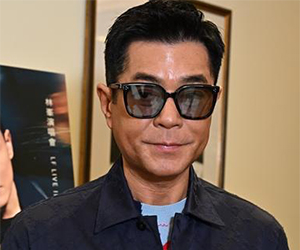【明報專訊】鞍山蒼蒼、吐露洋洋,位於香港中文大學本部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隨館藏漸增,歷經1988年、2007年兩期擴建後,近日再度建成新翼。但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下實現「天人合一」的理念,又如何延續建築與環境的對話,似乎並非容易事。
嚴迅奇手筆 山腰「地弊」變地利
館長姚進莊稱在文物館1971年成立之前,中大曾有一個名為「屋仔」的小型建築,專門用於冲曬菲林、裝裱和編輯工作。隨着文物館的成立,這裏逐漸成為校園文化命脈,被歷任校長譽為「中大之寶」。得以在大學核心範圍建立博物館,有義務、責任讓校內人士享用空間,加上近年博物館普及化為大眾公餘場所,研究型、教學博物館的使命,便是將大學教育及高水平的一些研究,推廣給更廣泛的公眾。比起迎合公眾口味,展覽更多是自身研究的延伸展示,為了令平日較少留意藝術的人都願意踏入館內,建築師的目光便顯得重要。
要在小於2000平方米土地面積建新翼,對建築師無疑是一大考驗。嚴迅奇約20年前曾為連接文物館展廳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做翻新工程,姚進莊稱嚴迅奇的設計跟校園環境和地理脗合,對整個氛圍拿揑得非常準,亦強調新翼的功能融合到校園,充分考慮了校園師生需求。中大依山而建,文物館則位於山腰核心地帶,姚進莊本認為這是文物館的地理缺陷,未料新翼縮土成寸、將地勢差距包在建築內部,巧妙地連結「大學道」及本部百萬大道,反而成了建築的優點。參觀者不會再感到上坡的勞累,他笑言「每一寸空間都用到盡」。自大學道拾級而上,進門甫見的是私密、休閒的空間,轉身一看,落地大玻璃外卻是一片豁然開朗的山景,在細小的空間裏營造兩種氣氛,姚進莊認為應歸功於嚴迅奇的奇思妙想。
新翼懸空留樹蹤 外牆皴紋如水墨
對嚴迅奇而言,「建築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藝術」,商業建築、校園建築、文化建築同樣圍繞着如何解決問題,再將解決的手法提升到藝術的層次。而文物館的建築比一般建築要考慮的東西更多:先是建築物的形象,再來是境界與氛圍,最後才是功能。
這次為賦予文物館新翼「起承立新」的形象,延續了著名建築師司徒惠設計中大早期建築時奠下的樸素風格,亦着意呼應功能性建築語言。在中大不少建築髹上新漆之時,新翼外牆沿用遮陽隔音的清水混凝土,未加多餘的裝飾,以樸實的材料與自然山體對話。而自大學道仰望,新翼懸浮於山坡之上,與本館連成一體,嚴迅奇說既寓意承接,也寓意向前展望,更有巨石浮在山坡、橫空出世的意境,宛如中國山水畫中巨石穿山而立的形態。因新翼懸空,造就了「石下留蔭」之境——下方步道的樹蹤未因建築物而打斷,一直延續。
中大的美學,亦在乎講「天人合一」。嚴迅奇稱整個箱形建築物的比例在大學裏面相對人性化,只佔路上小部分,不會因增建而阻礙山天相接的視野。而外觀看似樸素內斂,卻取法古代繪製山水畫的皴法,將水墨的質感印在外牆,再以斧劈皴紋上石頭的肌理,多出一種自然的體態。模仿古人畫石頭所用的「虎頭劈」皴法,成就外牆上粗闊深淺不一的線條,如同水墨畫濃淡有致。考慮到牆體會隨年日變色,如今不同陰影、深淺亦使之因應日照顯露不同神韻,大巧不工。
捷徑成藝術薰陶 V形柱轉化傳統
美觀及意境之外,是次設計也兼具實際功能。新翼樓底約4米半高的展廳處舊館的兩層之間,只需從舊館稍移半層就可到達,其後再拾梯便又抵達舊館的上層,展覽空間相互聯通、無縫相接,兩棟分開修建的建築渾然如一。館內大樓梯充當連接百萬大道與大學道的捷徑,嚴迅奇認為藝術需要薰陶,便藉提供便利讓學生看展覽和文化近距離接觸,走過行過自然會看一眼,或許會激發到具有潛質的學生。事實上,透過樓梯引導人從戶外拾級而上到室內的公共空間,再穿越到一個展廳展館的思維,亦是從傳統裏面找到靈感。他提到四合院、故宮等傳統建築空間的序列及組織,皆以一重重公共空間引導人探索,是次則以階梯在有限面積重現相近思維。又譬如傳統建築以斗拱支撐往外延伸的屋簷,則與這次以一個落點承托建築物V形柱精神相接,相比強行挪用舊日結構,嚴迅奇強調從傳統轉化出新意,以「起承立新」。
從大學站或大埔公路遠望文物館,姚進莊形容整座建築如同隱於深山的古寺,建築之靜謐與周遭的自然融為一體,認為是香港對於貝聿銘在日本建立美秀美術館的回應,希望擴建後的文物館能成為一片遠離繁囂、洗滌心靈的空間。悠悠長途重重山,獨立峻嶺間的一所文物館,靜待向行者娓娓道來千百年的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