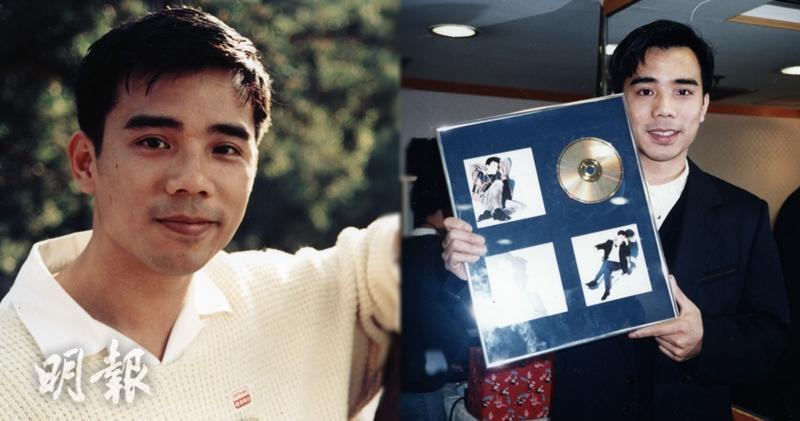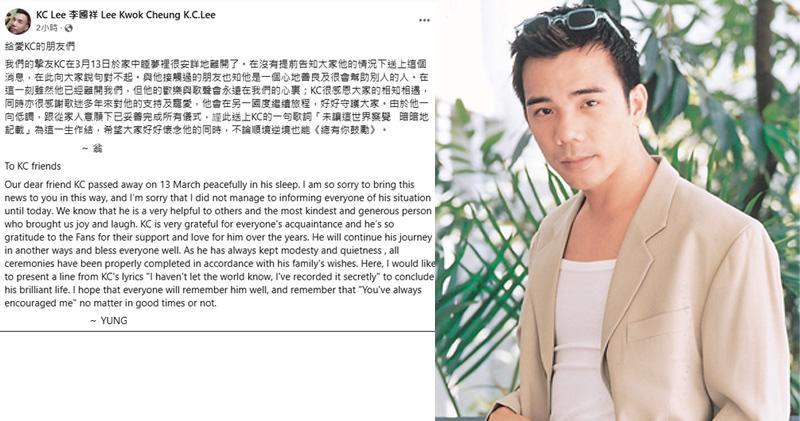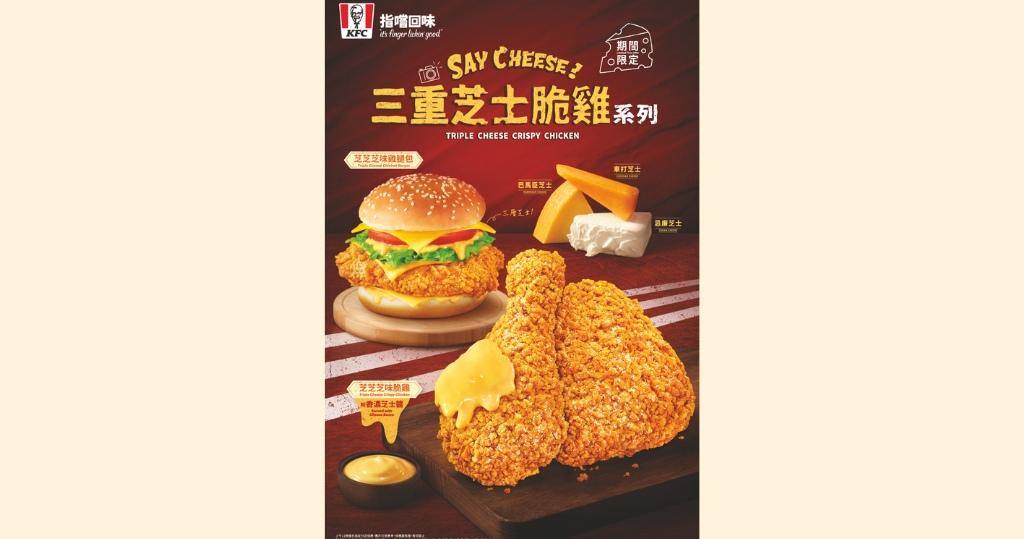【明報專訊】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3周年之際,不妨暫時離開24小時新聞,重讀已故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文章Un Occident kidnappé ou la tragédie de l'Europe centrale(「被綁架的西方:中歐的悲劇」,台灣譯本:《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昆德拉在該文由中歐小國的命運思考整個歐洲大陸的未來。何謂小國?他寫道:「小國是那種其存在隨時可能被質疑的國家;小國有可能消失,自己也深知這一點。」這段說話用來形容烏克蘭也恰當不過。
昆德拉揭示中西歐矛盾
昆德拉的文章聚焦於當時被蘇聯控制的捷克、波蘭和匈牙利,這三國的公民社會在鐵幕後奮力維持自身的文化和歐洲身分認同,抵抗蘇聯壓迫,並為此付出血的代價。雖然柏林圍牆1989年倒下了,但昆德拉文章所揭示中歐跟西歐之間的矛盾在歐洲整合過程中依舊鮮明,令學者不時重讀該文。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文章又多了一重意義。
之所以想起昆德拉這篇文章,固然是因為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美俄和談。以談判結束戰爭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因為目前俄烏均無法取得勝利,局面僵持,除了斷送更多人命外看不到出路。自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西方雖然給烏克蘭軍備支持,烏克蘭也善用新科技,以寡敵眾,跟俄羅斯大軍打成均勢,抵住滅國的命運。不過,西方始終忌諱跟一個擁核國直接衝突,戰爭陷入膠着狀態。
然而,和談還要看以什麼為條件和什麼方式進行。特朗普不理會歐洲盟友和烏克蘭自行主動提出跟俄羅斯和談,對侵略者俄羅斯無條件談判,還事先張揚可以解除制裁、共商投資計劃;反而對烏克蘭卻開天索價,要求烏克蘭跟美國簽訂礦產開發協議。特朗普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連番侮辱,斥他是獨裁者、挑起戰爭,言談恍如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發言人。這些行徑是否又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還是為了諾貝爾和平獎不惜一切向普京投降,且待觀察。但在大國博弈前,小國烏克蘭除了豐富的天然資源外,幾乎沒有籌碼。為了避免滅國,除了任由美俄兩大國擺佈外似乎已無他途。
不過,俄烏戰爭還有一個當事方:歐洲。但歐洲去了哪裏?歐洲才剛在2月14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被美國副總統萬斯教訓了一頓,聲稱歐洲「背離一些基本價值」、審查言論。儘管德法政客提出反駁,但在右翼民粹席捲歐洲的情勢下,歐洲右翼高舉捍衛傳統基督教價值的旗幟,與美國民粹右翼甚至俄羅斯在理念上產生共鳴。面對這樣的局面,歐洲精英卻遲遲未能提出有力的回應。面對特朗普大幅改變戰後大西洋安全機制、烏克蘭命懸一線,歐洲領袖雖然立即開會,但卻似乎一籌莫展。
且暫時離開當下時空,回到冷戰時代的歐洲。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鎮壓,昆德拉1975年離開捷克,由一個小國移居到文化大國法國,重新學習法語寫作,文化衝擊促使昆德拉思考歐洲身分。「被綁架的西方」1983年在Le Débat發表,引起很大迴響,翌年翻譯成英語在《紐約書評》刊登。這篇文章在1980年代曾引起歐洲知識分子大辯論,也預視了冷戰結束後西歐跟中歐國家的衝突。
俄代表「另一種文明」
中歐悲劇不在俄而在歐
文章以1956年11月蘇聯入侵匈牙利一宗事件開始:匈牙利10月革命反抗蘇聯,新政府更宣布退出《華沙公約》,但蘇聯當然不容許分手。蘇軍坦克11月開入布達佩斯鎮壓革命。匈牙利通訊社社長在辦公室遭蘇軍炮轟前發出一封絕望電報,告訴世人蘇聯正入侵布達佩斯,電報結尾是這樣的:「我們將為匈牙利和歐洲而死。」昆德拉反思:為何在這名匈牙利人心中,蘇聯對匈牙利的攻擊等同對整個歐洲的攻擊?他真心相信自己不僅在保衛匈牙利,也是在捍衛歐洲。但當時的西歐是否也這樣看待匈牙利的遭遇?這個問題引出了中歐與西歐間的隔閡。
地理上位於歐洲中央的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因被蘇聯劃入勢力範圍而被視為「東歐」。昆德拉認為,中歐小國歷經劫難,深知其存在並非理所當然,必須透過文化對歐洲的貢獻來證明自身價值。這三國的文化一直是歐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談到俄羅斯,昆德拉指出,儘管俄羅斯地理上部分屬於歐洲,但它同時代表着「另一種文明」。這並非否定俄羅斯的文化成就,而是強調其性格與歐洲文明的差異。俄羅斯自視為斯拉夫民族的中心,致力於將各異民族納入其帝國體系,追求「以最大的空間達成最少的多樣性」。相反,中歐則是「在最小的空間內實現最多的多樣性」,其文化多元性在1945年蘇聯統治下遭到嚴重壓制,對中歐人而言,這不僅是政治災難,更是對中歐文明的摧殘。
然而,西歐對中歐的奮鬥往往缺乏理解。昆德拉認為,這是因為西歐已不再以文化作為自身認同的基礎。中世紀時,歐洲的團結來自宗教,但啟蒙運動後宗教式微,文化成為歐洲的凝聚力。然而,隨着現代化進程加快,西歐的文化認同日益淡薄,歐洲的團結基礎也隨之瓦解。昆德拉最後回到1956年匈牙利通訊社社長之死,坦言:「對中歐的悲劇不在於俄羅斯,而是在於歐洲。」對該名社長而言,歐洲代表着偉大的價值,足以令他甘願獻身,但他不知道時代已經改變,歐洲不再是一種價值,他那句「為匈牙利和歐洲而死」在匈牙利之外並無人能理解。
昆德拉寫作「被綁架的西方」時,烏克蘭仍然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文章的焦點雖在中歐,但一個註釋卻提到烏克蘭:「歐洲一個偉大民族(烏克蘭人將近4000萬)正緩慢地消失。而這個巨大且幾乎難以置信的事件,卻在全世界未察覺的情况下悄然發生。」2022年的俄烏戰爭則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下發生。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歷史文化淵源遠較中歐國家錯綜複雜,要將之跟中歐國家比較自然不合理。但昆德拉對小國的分析及歐洲的被動,在這個時候讀來卻毫不過時。蘇聯打壓烏克蘭的歷史近10年才為世人注意,也成為烏克蘭重新建構身分認同的關鍵,跟俄羅斯愈走愈遠;但普京的俄羅斯卻緊抱不放,大談俄烏血脈相連,愛你才要打你。烏克蘭國土遼闊,但跟冷戰時代的中歐小國一樣,面對強鄰俄羅斯即使拚盡全力,也似乎難以扭轉命運。
歐洲依然無影無蹤
美俄對歐洲的衝擊並不始於今天。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已拋出要退出北約,我們早已不時聽到歐洲政客宣稱美國已不再可靠,歐洲必須自強,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都曾說過,德國下任總理熱門默茨日前也這樣說。但面對美國真的付諸行動,歐洲要怎麼辦?法國《世界報》引述政治學者Rémi Lefebvre形容法國精英對特朗普回應是「震耳欲聾的沉默」,他說:「我們正處於歷史的分水嶺,但精英們——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等——並未準備好迎接挑戰。這些精英看起來迷惘,就像被車頭燈照射的兔子,最多只會哀嘆,甚至有些完全認同萬斯的觀點——例如法國右翼。」時代不同了,但小國仰賴的歐洲依然無影無蹤;歐洲也無法回答昆德拉的詰問:歐洲究竟代表了什麼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