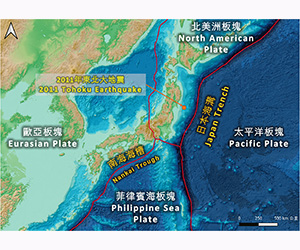【明報專訊】好像每逢談到他們都要「利申」,我算是YouTube頻道「試當真」的粉絲。他們幾年前開台時我尤其緊貼,但凡有新片必先睹為快。過去一年多反而看得較少了,不肯定是創作人還是我這個觀者出現疲態。也礙於代溝,有些片不明所以。最喜歡他們的「channel需要……」系列,從來覺得香港不擅出產好玩的偽紀錄片,該系列改變了我的愚見。
若沒記錯,試當真創辦人游學修一開始即揚言未來要拍電影。從經營YouTube頻道的角度,他們其實已經很受歡迎了。仍堅持要以拍電影為目標,證明「電影」、「電影院」來到網絡時代看似老派,始終還是有光環的一回事。
事實上,這說明兩個平台的差異。先不論成本及票房,只談發布的效率:網台、YouTube的反應快,創意、回應夠即時;相對而言,電影的循環太慢了,大費周章起碼一兩年才見成果。但也正因如此,電影比起網絡更需從長計議。網絡短片的零碎、新奇、信手拈來的主意,套到一個半小時的長片之上,能不能發揮效果?
試當真首部於戲院正式公映的電影總算出來了——《公開試當真》,英文名Once Upon a Time in HKDSE(蕩氣迴腸得有些誇張)。導演為梁奕豪(贊師父),監製有許賢、游學修、文永昌及陳溢朗。哈,第一齣竟然不是他們固所擅長的「偽紀錄片」而是如假包換的紀錄片。承上文的提問,《公開試當真》是從網片剪輯而成的。作為一齣紀錄長片,它如何?
命名題材見聰明
命名首先聰明,把「公開試」與「試當真」食字連在一起。「試當真」這個名字有戴頭盔的意味,先試試,卻也可當成來真的。失敗無妨,成功就是意外收穫。《公開試當真》有玩票成分,也有認真的一面——該台另一創辦人許賢,與2023年一個中學文憑試(DSE)考生滕毅康(阿康),在應考的4個月前一起發憤努力讀書,許賢甚至充當阿康監護督促角色。4個月時間全程跟拍,看看阿康最後能不能順利考入大學。
題材亦見小聰明。香港惡名昭彰的教育制度以及其公開試,香港成長的人誰沒牢騷?所謂的「教改」改來改去,新口號推陳出新、永遠的覺今是而昨非,倒頭來萬變不離其宗。許賢今年30歲,他是2012年的末代高考(A Level)生。不過無論我輩人參與過的會考、高考或今天的文憑試也好,有說求學不是求分數,騙人喇。過去與現在多少仍是一試定生死。成王敗寇,考生背負的重擔依舊。入大學仍然是高中生的標竿,趕不上才退而求其次。
由「應試教育」這個遊戲,衍生出連串光怪陸離的現象。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香港」的,付出只考慮立竿見影的收成:熟讀「遊戲規則」、雞精讀物、補習天王的補習班、past paper、marking scheme、貼題目、out of syllabus不要理會……教育還有什麼本質?誰在乎?縱使為官的及有關當局,早就不着邊際的把教學說成「學與教」,學生不見得多了哪些主導權。中學畢業前別管其他,先做好一台考試機器。
許賢中段一句話,勾起我的「公開試鄉愁」:「呢隻(為了答題不停)寫字的手,是教育制度下的產物。」對呢,我曾幾何時也有這隻手。我們當時同樣以寫得多、在試場舉手「加紙」而自豪,寫出什麼反而其次。足以證明,考試機制幾十年來沒改變。
在DSE眾多繁文縟節的前提下,《公開試當真》的阿康,臨急抱佛腳,注定要進行不可能的任務。阿康長得蠻帥的,當影片的主角不錯。他有演藝天分 ,因參加試當真2022年的「校花校草」選舉而為網民認識。他是個高中生,學校的足球代表隊成員。他似乎從來不關注學業(成績表例牌的形容詞為「無心向學」)。紀錄片前段蠻好笑的一幕,許賢帶着阿康找補習天王林溢欣(YY)幫忙。YY輕輕一問,阿康連中文科的「詩三首」的具體內容都搞錯。可見他作為應屆考生有多「業餘」。
業餘玩家視角窺探DSE
《公開試當真》嘗試從一個「業餘玩家」視角去窺探DSE。你一開始不全情投入的話,只會碰得一鼻子灰。然而即使投入,也未必有理想的結果。全片充斥不少soundbite,有些曾剪到預告片裏去。游學修說高中時想考入浸大的電影學院,偏偏公開試被物理、化學的成績拖累。他問這些科目與「讀電影」到底有何關係。另一受訪的比喻說制度設計者根本當考生是雞仔,對他們不認識、沒感情;篩選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被叮走。片首打出數字,每年5萬考生,只有一萬多人過關,其餘3萬多人被淘汰。
林溢欣不愧名師,思路清晰、出口成文,片中道出不少金句:「(文憑試)遊戲係考緊有限時間內,展現最叻的自己。」、「博盡無悔,重點是個『盡』字。」
問題也可能源於一個「盡」字。「為了XX可以去到幾盡?」不止大學,原來連中學都相當流行「博盡無悔」四字。這等潮語,只叫我們審視自己夠不夠瞓身、all-in;卻無從幫助我們決定內裏的核心價值。為何要考試?為何是這種形式的考試?為何要讀那些科目?……沒辦法,因為價值較抽象,瞓身、all-in具體得多。《公開試當真》初段,阿康半自嘲說,當下的動力已刻在自己名字裏頭:騰毅康的「毅」。
幾天前小學派位結果公布,幾個小六學生受記者訪問的片段,於網上瘋傳。有小學生一臉誠懇的說「讀書是我的本分」。真的?為何不是嬉戲?就當小朋友發自內心好了,如此「本分」觀念,從何時開始、被誰熏陶而建立的?
許賢說,10多年前考完公開試,筆記早已丟掉,母親的家只餘下唯一鍾情的經濟科。觀眾看《公開試當真》,不妨留到片末字幕最後,有個小彩蛋。我們都有類似經驗,不管小學、大學或持續進修,奮發一輪後,第一時間要把教科書及筆記置之不理、以至丟掉,甚或充滿恨意的燒掉!知識不過工具、求學僅是過程,喜歡與否根本無關痛癢。考試、成績才是最終目的。
除了死讀書,學校、師長、家庭有沒有責任去幫助學子培育個性、依據不同的性向,尋找自己真的喜愛的事情?我是誰?我之為我,到底與別人有何不一樣?除了本分,我們要不要也談談天職?就是說,我天生注定是個從事XX的人,在那個世界最自在,矢志不渝。現在的中學,不是都頗流行談生命教育麼?
但尋找意義談何容易?搞不好是一輩子的歷程,真不知學校能扮演多大的角色。不獨外力的阻撓,有時我們自以為找到,日子久了又不盡然。《公開試當真》的阿康,父母眼中他很醉心踢足球,他潛質不差,是學界代表。然而當他回說起來,卻是無可無不可的,看上去並不十分熱心。
當然,《公開試當真》關於制度的懷疑、成長的詰問,只透過受訪的片言隻語帶過,它的焦點終究是阿康準備DSE的歷程。
背上的「被拍同意書」
幾年前《給十九歲的我》掀起紀錄片倫理的爭議,《公開試當真》看來從《十九歲》的教訓學乖了。阿康的學校、校長等,影片沒拍得很詳,鏡頭有些避重就輕。讀網媒Wave的訪問,阿康中六的最後上課天,許賢在身穿的恤衫背面,寫上被拍攝同意書,給阿康的同學「簽署」(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天,同學各自在對方的校服上留言)。
許賢的行為固然是鬧着玩的,絕不代表影片沒有道德的斟酌餘地。例如,阿康以4個月時間認真準備DSE,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可是外人看來,許賢、「試當真」給與他大量幫助與資源。阿康於心有愧,他不止一次在鏡頭前自責、流淚,怕自己辜負了「大好機會」。
另外,紀錄片的鏡頭介入現實,少不免都有干預的成分。阿康因「校花校草」選舉後薄有名氣,街上有人認得他。阿康備考的過程有YouTube頻道全程跟拍、定時剪好上載,群眾的認識與無形的期許,無疑也對他構成壓力。他放榜後有說到的,自己對成績有期望,惟別人的期望更高。
後段阿康由於睡眠不足而發生小意外,跌至口腫鼻青。為此,許賢再次登門造訪阿康的父母。始料不及的是,阿康父母相當「通情達理」,倒過來憂心兒子的意外,給許賢帶來過大的壓力。
《給十九歲的我》女生關心紀錄片呈現出自己的怎個形象,阿康照理也有同樣的疑慮。他的故事被電影、銀幕放大了,今天人人見證他4個多月來應考的困頓、沮喪。網片的生命力未知,可電影真有機會流芳百世的。阿康往後要有心理準備,不論多少年、他成長到多少歲後,仍會有人看到、重提影片,按裏頭的線索去認識他。那個2023年的「自己」,會跟他形影不離,不斷跑回來纏擾。
我反覺得《公開試當真》最好看是許賢與母親的段落。許賢母親健談率性,回首兒子成長,她有不少自嘲與自省,許賢大概沒想到母親會在鏡頭前懺悔。許賢本人性格戇直可愛,講話慢條斯理的;時而木訥,時而像冷面笑匠。透過《公開試當真》,他有機會回溯自己從事網媒創作的路,認清多年來,為何自己一直對公開試的議題念念不忘。創作得以認識自我、療癒關係,這乃創作人莫大的福氣。許賢當年若按意願去念經濟、從事有關行業,說不定一輩子也遇不到此契機。
不過不失 能登大雅之堂
《公開試當真》作為試當真首齣長片,不過不失,能登大雅之堂。故事出發點稍為站不住腳,阿康若備考的時間更長,故事才更見真章。可能拍攝需時,幾個攝影師輪替,影像質素有時稍見遜色。剪接恰如其份,他們竟找來張叔平來拔刀相助(與另外三人合剪)。我沒有看過YouTube的原裝長版本,今天把幾個月的故事剪來,敘事穩陣。序幕先交代阿康與許賢應考DSE的第一天,然後再由4個月前細說從頭。全片剛好個半小時,放映一小時,敘事回到片首的起點。
最後15分鐘為高潮所在:終於去到DSE的放榜日。放榜日的氣氛不錯,阿康雖然一臉凝重,陪在他旁邊的,包括許賢,全部默默支持他。他們知曉分寸,不嘮嘮叨叨、隨便的曉以大義。
未知原本的YouTube片如何,現在全片以CinemaScope的闊銀幕比例剪成,不知是不是與張叔平有關(據說「阿叔」喜歡叫年輕導演把影片裁切成闊銀幕,使看上去更具電影感)。出奇地全片配樂不算多,片尾rap曲《5**》很清新。
試當真形象年輕,他們深明自己的市場定位,對中學生別具吸引力,是以由「校花校草」選舉到《公開試當真》都非常切合他們的口味。也難得香港首次有齣紀錄長片,嘗試以小見大,喚起坊間對教育/考試制度的注視與討論。無論如何,《公開試當真》誠意可嘉。
本周三7月17日就是今年DSE放榜了,考生、他們的師長與親友不妨去看看本片,互相了解、安慰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