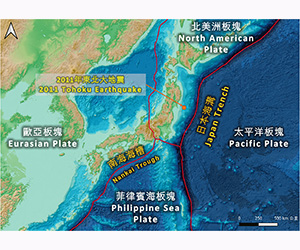【明報專訊】我第一次見到聶華苓的時候,她已經92歲了。2017年秋天,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IWP)舉行50周年慶祝活動,一直嚮往IWP的我有幸獲邀到愛荷華城採訪。飛機沒有延誤,但我還是來得太晚,聶老師在我出生以前已經從國際寫作計劃總監一職退休,來到2017年,她亦不再經常參加公開活動。不過,她仍是廣受尊敬的IWP共同創辦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無論她是否在場,IWP活動主持人的致謝辭都總會提到「Hualing」這個名字。專程來參加慶祝活動的華語作家,包括1967年參與第一屆駐留的台灣詩人瘂弦,還有香港作家董啟章、潘耀明,內地小說家畢飛宇、李笛安等。他們在愛荷華的那幾天,除了參與慶祝活動,亦會跟聶老師及親友一起到Paul Engle墓前致意、到聶老師的家「安寓」聚會聊天、外出觀光等。同樣長着華人面孔的我,因着記者的身分獲許混在其中一同參與,尋找機會訪問聶老師。